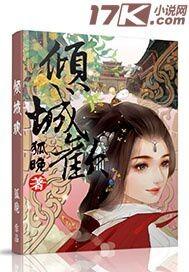.co 达公公轻轻敲了敲绣梅馆的门,身后跟着刚从宫外头请回来的年太医。绣梅馆的门开着,他去叩门只不过是为了让余香听个响,以此证明他没有不将余香放在眼里。
他的确不喜欢余香,可太子殿下既然能够听从余香的要挟,让他特意将年太医从宫外请回来,就说明太子殿下心里根本放不下这个女人。只要太子殿下一天心里还有这个女人的位置,那这个女人便随时都有翻身的可能,他不得罪,是给自己留后路。
余香的嘴唇已经干裂的厉害,刚才她用沾了水的湿帕子狠狠擦过,可是无济于事。一整日滴水未进,又值盛夏,她的嘴唇如同干旱已久的土壤,岂是几滴雨就能够滋润的?
她坐在床边,望着站在门口叩门的达公公,不明白他这般多此一举是为了什么?大门敞四开,你自进门来,好端端的,敲什么门?
可是当余香看到达公公身后跟着的人时,眼睛却一下子亮了起来,太子竟然真的同意将年太医请来了?
“臣年昱见过太子妃娘娘,臣见娘娘脸色不佳,还请劳烦娘娘伸出手臂,容臣为您把脉。”年太医看着余香憔悴的面容,不知道这短短时间内发生了什么?这太子妃刚刚怀上身孕,按理说正应是得宠的时候,那日看她气色还是大好,今日是怎么了?
余香望着达公公,而后开口道:“多谢达公公跑这一趟,太子殿下一定等你等得着急,就别在我这小屋内瞎耽误功夫了,去忙吧。”她有一肚子的疑问要对年太医说,更有一肚子的秘密要对年太医讲,若是达公公在场,她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一字不漏的传到太子耳朵里,本就是误会深重,她总不好再生事端。当然,她也知道此时出言赶走达公公,必定也会惹来猜忌。可是那又能如何呢?这已经是没办法的办法,她总不能让达公公看着自己递给年太医的那张纸条,并亲耳听到自己要年太医将纸条转交给周子欢吧。
达公公也识趣,道了一声告辞转身便走,心中却惦记着要将此事一字不漏的传到太子耳朵里。到底有什么背人的事情,还怕别人在场呢?怕是用脚趾头想想也猜得出来,还不就是假孕事情败露,她需要找个机会跟年太医统一口径,千万不要说出假孕的事情来。就说是年太医诊错了脉,或者是服错了药,搞得那日乱了脉搏。这样的事儿在宫里并不新鲜,听的也好,见的也好,多了去了。
达公公冷哼一声,心中觉得这个余香也并没有聪明到哪里去,太子之所以会对她情深几许,也不过是仗着她年纪小,颇有几番姿色罢了。
余香见达公公的脚步声走远了,才将手腕递给年太医,等他诊脉。
她没有提起方太医的事情,也不知道年太医随达公公这一路前来,有没有听闻这件事情,但是她没有主动提,她在等着年太医亲自开口告诉她真相。
有喜的事情打从一开始就是年太医起得头,余香才是那个被蒙在鼓里跟着人家走的人,所以现如今出了事儿,纵然被拖下水,也该一起才是。如此方算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日听闻余香有喜,太子赏赐了年太医好大一笔金银,今日年太医总该为了这笔赏赐,给个说法才对。
年太医在余香手腕上盖了帕子,而后伸出手指在余香的胳膊上寻脉,屋内静得就算是掉落一根针的声音也听得见。没多大会功夫,年太医收回了手,将那帕子掀起来,脸色不大好看。
年太医欲言又止,最终长叹一声。
“我可是身患什么绝症了,以至于让年太医说个病情为难成这个样子?”余香的话轻描淡写,不以为然。心中却早已料定,还不就是年太医忽然发现自己诊错了脉,孩子消失了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怎么当日就不能认认真真把个脉?饭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说,他知道因为自己随口的一句话,带给了人多大希望吗?现如今这希望落空,那存留下来的失望又要人如何承受?
年太医抿着嘴唇,像是下了好大决心道:“娘娘,臣接下来说的这番话并非好消息,您可是要有个心理准备。”
余香点头,心道你要说的坏消息,我早已听过许多遍了,不需你讲,我都能一字不漏的重复出来。
年太医见余香点头,于是蓦然跪地说道:“臣刚才为您诊脉,发现您的脉搏非常虚弱,滑脉之感时有时无,加之听闻达公公路上对臣讲,您昨日昏倒在地,身下有血迹,微臣以为,这是小产的征兆。不过娘娘放心,臣等当竭力为您保胎,但能不能熬得过这三个月,臣无法作保。如果娘娘能接受,选择不要这个孩子,臣也有不要的法子。毕竟娘娘还年轻,日后的机会多得是,未必非要急于一时。等待调理好身子后,再怀也好。”
“你说孩子现在还在我肚子里?”余香怕是自己理解错了意思,又落得个空欢喜一场,故而连忙选了最直白的方式问了出来。
年太医点头,又道:“但臣刚才说了,因为娘娘身子虚弱,情绪起伏又大,此胎还出现了小产征兆,保住的可能性不大。”
“今日方太医来为我诊过脉你可知道?”余香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现如今年太医的话可谓是她的全部希望,她不能就此撒手。
“臣刚从家内赶来,还不曾听闻方太医来为娘娘诊脉一事。看娘娘的表情,可是方太医说了什么与臣不一样的事?”年太医斗胆猜测道。这两年来,他跟方太医的意见向来不合,他为人治病一向主张尝试新的方子,而方太医却是个遵循老理的人,无论开什么方子,问什么药,都得按照古医书上来,半两也不能有变化。不过年太医心里也奇怪,现在宫内的主子都知道方太医年岁已高,看病不准,在去太医署请人的时候往往会刻意避开他,今日为什么会有人特意请了方太医来为太子妃看病呢?难不成是故意的吗?
“年太医快起来坐吧。今日方太医为我诊脉过后,笃定声称我没有怀孕,衣裙上的血迹不过是月信所致。”余香觉得简直是天意弄人,如若今日在太子面前说出脉象结果的人是年太医,那此时此刻,她的日子会不会又是另一番光景?后日就是她跟太子的大婚之日,现在应该有人来为她裁喜服,对婚词。而她,只该踏踏实实待在这绣梅馆内,做一个最美的新娘子。可是现如今,太子丝毫不再信任她的话,一场没有情意的结合怎能换来白头偕老?她的大婚之日,难道不是即将成为她幸福的终结吗?
年太医谢恩过后,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余香对面,而后道:“屋内没有别人,娘娘也别怪臣多嘴,方太医年岁已高,眼神不济,脑子都不是特别清楚,他说的话并不能全信。娘娘怀胎时间尚早,脉象不是特别明晰,加之您身子虚弱,这寻常大夫若是不注意,还真容易将您有喜的脉象忽略过去。经由臣手把出喜脉的人不说上百,也有几十,算得上是这方面有经验的太医了,娘娘该相信臣的话才是。”年太医一脸认真的对余香讲着,说话之间望着余香那惨白的脸色有些出神。他以前有个女儿来着,叫丹儿。后来一场大病夺走了她的性命,可在女儿大病之时,他却还在宫中为了感染风寒的皇帝而煮药,回府之时,女儿已经离开一日了。他总想着,若是他早回去一些,多给他一点时间,他就能想出医治女儿重病的法子,那她就不会那么小便离开自己。若是她还活着,只怕也跟太子妃一般年纪了吧,也是风华正茂,该许人家了。太子妃现如今都已经是即将做娘的人,可他的女儿却还不知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孤孤零零的飘荡着。
“年太医,你怎么了?”余香伸手在年太医眼前晃了晃,不知他因为想什么而如此愣神,但心中听到他说的话,却也是觉得欣喜。
她伸手轻轻抚上小腹,那里还是十分平坦,但她知道,在这里的深处,有她跟太子生命的延续。
年太医回过神来,连连道:“没有什么,娘娘放心,臣定当竭力为您保住这个孩子。”
“年太医,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求你帮忙?”余香伸手摸了摸刚刚解下来放在枕边的荷包,对年太医说道。
“娘娘对臣有什么要求只管吩咐,怎敢说是请求?”年太医越看余香的模样,越觉得像是自己的女儿,若她真的是自己的女儿该有多好。虽说这宫里也是个吃人窝,可到底她还健健康康的活着啊。
余香将那荷包递给年太医道:“还请年太医将这荷包转交给关内侯大人。”
年太医望着余香手里捧着的那个小小荷包,他虽然猜不出这荷包内到底装了什么,但也猜得出此事非同小可,否则一个当朝太子妃,怎么会对一个小小太医说请求?他心下一横,为皇家效了这么多年的忠,这一次就算是他为了自己,也任性一回。不管皇家,不顾朝权,帮她这个忙吧。谁让她长得那么像自己的女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