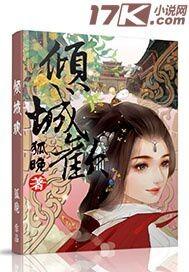.co 余香瞪着一双因为憔悴而熬得血红的眼睛,她就那么看着太子冷漠的模样,觉得温暖如春的太子怎么顷刻间变成了一个如同二皇子一般的人?不,二皇子只是让人觉得寒冷,而此时的太子却让人觉得疼。
原来他也是会伤人的啊,而且他伤人伤的还是这么深,这等深厚功力,让余香一瞬间意识到自己原来还是太嫩了。
余香试着站起身,但她却觉得下腹酸痛,腿也无力得很,想要站起来怕是不大可能。所以,她就用双手在地上蹭着,将自己移到了床边,而后靠着床榻,将自己缩成了一团。
听到声音,太子回头望着余香的举动,想要上前扶她,却到底忍住了脚步。“天宁,你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博得本宫对你的同情?本宫的话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
余香听见太子的话,冷笑出声,心里喃喃念着:我需要博得你的同情吗?你的同情是能用来当饭吃,还是保我不伤不死?
此刻,余香忽然懂得了萧芊芊当年对待子欢的感情,当爱你爱到死心塌地,就是等于将一个完完整整,毫无保护的自己交给了你。在我赋予了你爱我的权利时,便也赋予了你伤害我的权利。
所以说,太子殿下,其实你在意的原本就只是这个凭空出现的孩子,并不是我,对吗?
故而在听到这老太医随口一句,我根本没有怀上孩子时,你便是觉得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浑身上下再无可信之处?
我不必问,你不必答,结果不是已经了然了吗?
“臣妾要见年太医,否则宁愿太子殿下赐臣妾一死。”余香抬起头与太子四目相对,缓缓开口,却语调清晰地说出了这句话。
太子望着余香眼神里的倔强,是,这的确是他爱的模样,可是此时此刻余香执着的念头却是令他痛心不已。事情既然已经败露,你还要见年太医做什么呢?纵然你说服了年太医,胆敢犯下欺君之罪来欺骗本宫,又有何意义呢?更重要的是,“天宁,你是在威胁本宫吗?”
“是,臣妾在以性命作为要挟,太子殿下可以听,也可以不听,选择权在您。”以她现在的身体情况,肯定没有力气走到太医署。更何况,她没有出入储宫的腰牌,正值这个关口,福子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将他的腰牌借给自己,所以,只能自己以身试险,赌上一把了。
如果赢了,她就能见到年太医,就可以知道自己怀孕一事是真是假,也可以摆脱他将纸条转交给周子欢。
可如果赌输了呢?不知道,余香没有设想过自己会输。输人不能输士气,任何一场赌局在未开始以前你都不能认为自己必输无疑,否则老天看到,必然不会帮着你。你得认为自己一定会赢,且必须要赢,而后拼尽全力。
太子凝望了余香一眼,而后一甩袖子,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绣梅馆。
余香的心落了地,砸得心坎里生疼。这一局,是自己赌输了吗?她低头望着自己衣服上的血迹,肩上的头发因为没有束起,早已披散下来。不需照镜子也知道,她此时此刻有多么狼狈。
屋内转瞬又空无一人,靠不了她便靠自己,这么些年她也是一个人熬过来的,这又不是头一遭,有什么了不起?
她双手扶着床沿,胳膊一使劲儿,站了起来,就这么一下,便有冷汗从额头渗出来。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她身子怎么会这么虚?余香不懂医术,自己虚弱成这个样子,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她扶着屋内一切可以借力的东西,桌子,椅子,而后蹭着步子走到水盆前,她伸手探向那盆里的静水,唇边咧开一个笑容来,这水盆正对着房门的位置放着,这一上午被太阳晒得温了,刚好可以来用。
余香将帕子放到水盆里,沾湿了,而后擦干净自己的脸,然后她走到衣柜里,找出了一条新衣裙。
不管到什么时候,就算是死,你也不能让别人看出你的狼狈来。万一没死呢?万一置之死地而后生呢?你日后总还是要抬头见人的,你若是想成为高高在上,低头见人的那一个,就不能留给别人那么多话柄。
今日变成这副模样,并非出于她的本意,既然自己还有力气可以动,就该让自己干净一些。
换下衣裙的时候,她望着裙子上的血迹出身,她肯定那不是月信,可是血又不多,究竟是因为什么?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怀了孩子,小产了吗?一想到这儿,她的心里便觉得堵得慌。
绣梅馆外,太子突然停住了步伐,站在那儿,许久没动。
达公公上前一步道:“太子爷,奴才要帮天宁姑娘请年太医吗?”揣测主子的心思,是身为内臣要学习的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叫做“服从”。
太子长叹了一口气道:“随她去吧。”而后,他快步走向了正殿的方向,将达公公一个人甩在身后。
安明殿内,二皇子摆弄着手里的香炉,听着来人对他一一汇报储宫的日常。
“天宁被安阳请去喝茶?安阳那丫头心高气傲,无端端的哪里会请天宁喝茶,只怕是有求于她,说白了还是为了卫婕妤的事儿。此外呢,可还有别的稀奇事儿?不是说天宁的孩子流产了吗,最后保住了没有?”二皇子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忽然就对余香的事儿如此好奇起来,他安慰自己,也许就是因为她即将成为太子妃吧。其实皇上寿宴已过,莎罗又顺利安插进储宫,他此时大可全身而退,继续出宫戴上他的那张银色面具,做一些急需他做的事儿。可偏偏他此时此刻还真就不想离开这宫里,宁静了许多年的未央宫,忽然就被这一个莫名跳出来的小丫头搅了个天翻地覆,这事儿不是挺有意思吗?这样的故事,可是他身在宫外瞧不着的。所以宫外面的事情,就暂且拖一拖吧,交给赤鹰、绿豹他们去做就好了。
“回主子,今日太子请了方太医过去把脉,方太医说天宁姑娘并未怀孕,裙子上的血迹不过是来了月事造成的。”那人垂着一张脸,俯首着,事无巨细的回答着他所知道的储宫所有大事小情。
二皇子听了这话一声冷笑,“方太医?谁出的馊主意,那老头早是一条腿迈进棺材的人了,他把的脉也有人相信?天宁若是想要假孕,那大可以在父皇寿宴之前说出来,那岂不是更有利于巩固她太子妃的位置?她怎么会蠢到在父皇已经钦点她为太子妃之后,寻了个假孕的借口?不过,就凭借太子的脑子,又相信了方太医的话吧。”
那人愣愣地望着二皇子的神情,捉摸不透主子的心思。主子不是一直非常讨厌余香吗?他不是一直将这个女人视为背叛过他的人吗?为什么当他听到这个女人被人误会的时候,却流露出了一丝不悦呢?“是,太子对方太医的话无比相信,当前便认为是天宁一直再欺骗他,故而已经跟天宁处于冷战的状态。由此来看,天宁未来的地位不会牢固了。”
二皇子望着自己手中香炉内的香灰逐渐落成了十字形,就像是两条线,相遇后又各奔东西。他脑海中竟然闪过了一个诡异的念头,他要不要此时出手,帮余香一把呢?
可是下一秒,他便决定收回这个愚蠢的念头,自己为何要插手到她跟太子之间呢?无论是太子除掉余香,还是余香除掉太子,这不都是自己想要看到的局面吗?他们应当自相残杀,而不是携手相爱,不是吗?
二皇子将手中的香炉放在一旁,拍了拍手上的浮灰道:“你可隐瞒了我什么事情?”
那人愣了一下,而后摇头笃定道:“奴才不曾隐瞒过主子什么。”
二皇子眯起眼睛,唇边闪过一抹稍纵即逝的笑容,而后道:“那就好,你回去吧,出来久了,免得被太子发现。”
那人“喏”了一声,转身离开了安明殿正殿。
望着他渐渐消失的背影,太子拿起手中的银勺在香炉里胡乱划着,他当然知道那人隐瞒了自己什么,余香手中有一块丹书铁券,这么大的事儿他竟然没有告诉自己。
多有趣,一向听话的狗,如今竟然也要换主人了吗?他倒是觉得这宫里的戏,越来越精彩了。
“主人,接下来您需要我做什么?”莎罗从正殿的屏风内走了出来,乖巧地站在二皇子面前。
“除了盯紧太子,还要盯紧他,看看他到底在跟本宫隐瞒什么。”二皇子看也不看莎罗,只顾低头拾掇那捧香灰,可别小瞧了这香灰,这可是整个汉王朝都寻不来的香料。
莎罗点头,声称明白,而后留恋地望了二皇子一眼,自安明殿后门离开了这里。
二皇子敢让莎罗替她办事,原因很简单,他知道莎罗钟情于自己。女人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所以没有奴才会比莎罗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