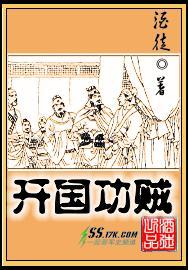.co “是!”站在帐篷外的侍卫听到窦建德火,赶紧小跑着冲了进来,取了窦建德临时写就的手令,然后小跑着冲入了黑夜。
聊城到安阳的直线距离都有五百二十余里。传令的侍卫沿途跑死了五匹珍贵的战马,才于第三天早晨赶到目的地。留守郡城的长史姓崔,是郡守大人的女婿。见到钦差莅临,赶紧恭恭敬敬地迎了出来。
传令的军官是窦建德从豆子岗带出来的老兄弟,最看不上前隋的降官,将崔长史的胳膊向旁边一扒拉,低声喝问道:“别废话,麴太守在哪。王爷叫他当面阅读手谕!”
被一个小小的校尉当众给脸色看,崔长史丝毫不觉得耻辱。躬身作揖,陪着笑脸解释道:“钦,钦差大人有所不知。麴太守一心为国,昨天正午……”
“都叫你少啰嗦了。直接说,太守大人去哪了。别扯文的,咱听不懂!”传令钦差竖起眼睛,大声命令。
“谨,谨遵上差吩咐!”崔长史又做了揖,把礼数补足了,才慢吞& {}吞地说道:“太守大人带兵攻打滏阳去了。昨天中午出,现在估计……”
“你***,还啰嗦个屁!”钦差一脚踢翻崔长史,飞身跳上战马,“把城里能跑的牲口都给老子牵出来,跟老子去追麴稜。若是他被程名振打败了,你等一个也甭想活!”
“太守带了一,一,一万五千人,姓,姓程的才,才……”崔长史在地上打了个滚儿,结结巴巴地回应。传令的钦差根本不肯再跟他废话,拨转坐骑,带着几名已经累得不成*人样的侍卫冲着北方狂奔。
见对方越跑越远。崔长史终于明白过些味道来,拍了拍身上尘土,骂骂咧咧的道:“粗坯,真是粗胚。老子是读书人,不跟你一般计较。来人,把驿馆里边送公文的战马全拉出来。跟我去追太守大人!”
底下小吏一听,赶紧去驿站去拉坐骑。手忙脚乱折腾了小半个时辰,终于选出四个身手灵活的家将,拥着崔姓长史,每人三匹快马,沿着官道“保护”已经去远了的钦差大人。
这条官道是大隋全盛时所建,年初的时候,窦建德为了方便商旅的通行,又专门派人修葺过,因此十分平坦。十几匹战马撒开了四蹄狂奔,两个时辰后,终于追上了钦差大人和他的侍卫。双方汇集在一起,又沿着官道追了一个多时辰,终于在下午申时,听到了前方的号角声。
“***,连个监视四方敌情的斥候都不派,还好意思跟程名振伸手!”钦差一看麴稜的战旗,立刻破口大骂起来。“麻利着,再坚持一下。堵住了麴稜,老子请你们喝酒!”
“诺!”侍卫们答应得有气无力,强打精神往中军方向冲。还没等靠近大队,耳边猛然又听见一阵激昂的号角,“呜呜,呜呜,呜呜——”
“打起来了,手谕作废。全体拔刀,准备保护姓麴的王八蛋!”不愧为窦建德的心腹,钦差一听见号角声,就知道敌军已经起了进攻。赶紧改变命令,以避免大伙乱了自家军心。
“奉窦王爷的命令,前来保护太守大人!”亲卫们的反应也非常敏锐,拔出兵器后,立刻扯开嗓子自报家门。
“奉窦王爷的命令,前来保护太守大人!”
“奉窦王爷的命令,前来保护太守大人!”
孤零零的喊声很快被前方的号角与战鼓声所吞没。不远处广袤的冬野上,几队全身披甲的精锐士卒,迈着稳定的步伐,一步步向麴稜的队伍推将过来。
斜阳西坠,未到傍晚,彩霞已经烧遍了天空。
魏郡太守麴稜突然现自己的嘴巴有些不听使唤了,费了好大力气才能张开,结结巴巴地憋出了几个字,“谁,谁当先锋?本,本官一定向夏王保,保举他!”
“大人,我军人数多,应该先用羽箭射住阵脚!”郡丞张翼文是当地豪强的一个庶出的儿子,多少懂得些战阵之事。见麴稜实在紧张的不成样子,主动上前,大声建议。
“那,那就放,放箭!快,快放箭!”麴稜记得都快哭出来了,跺着脚命令。他万万也没想到,程名振麾下的五千士卒,居然敢半路截杀自己。而自己所带领的人马虽然是对方的三倍,但是把阵势一拉开后,差距居然如此明显。敌人毫无畏惧抢先起了进攻,自己这边从上到下却个个都在筛糠。
“不能放,敌军还在一百五十步之外。羽箭穿不透皮甲。五矢之后,弓箭手力竭,势必为敌军所趁!”郡丞张翼文扯了麴稜一把,急切地劝阻。
“那,那可怎么办啊?”闻听此言,麴稜愈地没有主意了,带着哭腔问道。
传令的钦差恰好挤到他的身前,听见对方如此孱弱,推开麴稜,一把抢过中军令旗。“中军站立不动,长枪上前结阵。左右两翼,压上去,包抄敌军!”
“你!”麴稜转过脸来,立刻看到一道恶狠狠的目光,吓得把所有叱责的话全憋回了肚子。
“他是窦王爷的侍卫,前来保护太守大人!”崔长史跑得只剩下半口气儿了,怕此刻太守大人再弄出什么给大伙长脸的事情来,喘息着低声解释。
“窦,窦王爷的侍卫,来,来保护我?”麴稜满脸难以置信,指着自己的鼻子问到。
“大人请上马!”钦差没时间再搭理他,命令两名侍卫将麴稜驾到马背之上,一左一右紧紧夹住,摆出一幅随时会领军冲击的英勇架势,然后快挥舞令旗,“两翼继续向前,中军,中军的弓箭手,前方一百二十步,羽箭遮盖,射!”
“前方一百二十步,射!”底层的几个小军官看到中军旗号,立刻将命令传了下去。
冬天的日光不强,但面朝太阳,来自魏郡的乡勇们依旧被晃得张不开眼睛。听到上头的命令,把手一松,管他三七二十一,将羽箭一股脑的射了出去。
数千支羽箭腾空而起的威势不可谓不大,霎那间,头上的日光都陡然暗淡了一下。可羽箭落下去的效果却实在乏善可陈。大多数箭矢没飞过五十步,就掉头扎了下来。零星几个勉强飞到了正确目的地,度却已经慢得无法再慢,被对面的洺州子弟用刀一拨,立刻懒懒地掉了下去。
“你选的什么兵?”钦差气得大叫。挥动令旗,继续大喊,“射,射,别停下来。把箭馕里的弓箭都给老子放出去!”
这种战术倒恰恰适合魏郡众乡勇的真正实力。弓箭手们闻令,再不管什么轮射、截射、阻断射。张弓搭箭,将箭馕里的雕翎一股脑地向对面射去。
冰雹一样的羽箭下,洺州士卒脚踏鼓点,继续前进。丝毫不管袍泽就在身边倒下,丝毫不看从两翼慢慢包抄过来的敌军。他们眼睛里只有一个目标,麴稜,麴稜,高高跨坐在战马上的敌军主帅麴稜。取其级,敌军自散。一万五千和一千五百之间没什么区别。
魏郡太守觉得自己好像被一头猛兽盯上了霎那间肝胆俱裂。他第一反应是拨转马头逃走,却看见左右两侧侍卫手中明晃晃的横刀。他想向窦建德派来的钦差说几句乞怜的话,张了张嘴巴,却现自己压根不出任何声音。
敌军还有八十步,双方还没有生实质性接触。麴稜却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根本看不到活着的希望。他现在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没听城内几个大户的劝解,不要冒冒失失地出来抢什么功劳了。他记得自己当时还讥笑那些劝告自己的人,被一个*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吓破了胆子。现在却终于明白了,人的本事并不长在年龄上。有人年过半百,却除了会做官之外什么都不会干。有人不过二十出头,却犹如*虎啸谷,天地为之色变。
五十步,洺州营勇士步伐不变,继续前进。四十步,洺州营的勇士跨过受伤的袍泽,继续向前。三十步,二十步,终于,魏郡太守麴稜的嗓子能出了声音,像杀猪般惨嚎起来。他知道自己这样做很丢人,却没有其他任何手段来缓解心脏上所承受的压力。
“啊啊啊——”麴稜厉声惨嚎,同时被自己的举止羞得无地自容。但没有人回头看他,对面的洺州勇士终于开始冲锋了。一手举着横刀,一手提着圆盾,嗓子里喷出猛兽的怒吼:“啊——啊——啊——”“啊——啊——啊”
人未至,声浪先到。犹如有实质的巨浪般,轰然拍在了魏郡乡勇的脑门上,将仓促组织起来的防守人墙拍得摇摇欲坠。几个心智不坚定的农夫丢下兵器,双手抱着耳朵蹲了下去。更多的牙关紧咬,苦苦支撑,手中的兵器却不停地上下颤抖。
红彤彤的烟云下,洺州弟兄从夕阳的光芒中涌出来,撕开一切险阻,将魏郡乡勇冲得人仰马翻。
一鼓,阵破,窦家军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