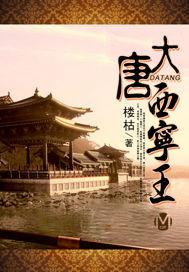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水清姑娘,深更半夜的这是去哪儿?”
说话之人名叫祖冒,原是河东节度使牙署的一名牙将,与契丹交战时被俘,后辗转到了李少卿胞弟李阳九帐下效力。
“我去哪跟将军有何干系。”浅水清镇定地答道。
“姑娘如今是大将军跟前的红人,你去哪跟我是没关系,可是这几个人就跟我有干系了。大将军有令,杨昊家人的安危都着落在二将军头上,二将军又把这事落在我的头上。水清姑娘如今要带她们走,我不该来问一句吗?”
“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兵荒马乱的,二将军几位挂念几位夫人的安危,特遣末将来接几位夫人到营中小住几日。”祖冒阴阳怪气地说道。
“多承美意,我们自己还能照顾自己。”晴儿说完,转身对众人道,“快回院去。”
“且慢!”祖冒一声断喝,士卒们立时拦住了晴儿等人的去路。
“你们想干什么?!”浅水清厉声叱道。
“干什么?”祖冒一声冷笑,“请几位夫人回营。”众士卒一拥而上。
“住手!”浅水清一声尖叫,拔出匕首对准了自己的咽喉。众人都吓了一跳,晴儿忙劝道:“妹妹别这样。”小鱼慌忙去夺刀,却被浅水清阻止。
“你听着!”浅水清指着祖冒的脸,“放了她们,否则我就死在你面前。”
祖冒听了这话悚然一惊,浅水清如今可是李少卿面前的大红人。大将军为了她可是一连三天不见外人了,这对刻苦勤政的大将军来说,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倘若浅水清因此而伤了自己,自己这条命还要不要了?
“水清姑娘有事好商量,先把刀放下来,别伤了自己。”
“你怕了?”浅水清冷笑一声,扬起了左手,“看到没有,大将军送我的翠玉手镯,大将军答应娶我了,你要是逼死我。只怕一百颗脑袋也不够砍的。”
浅水清手腕上戴着的一对翠玉玉镯确实名贵异常,但究竟是不是李少卿所赠,只有天知道的。
“我数三声,你们立即退去。否则我立刻死在你面前。”不知怎么的,浅水清这话中有一股冷森森的鬼气,不光祖冒听着心惊胆战,晴儿等人听来也是只打寒颤。
“我走,我走,”祖冒一边说着,一边果真往后退去。
“哈哈哈,水清姑娘何必动怒呢。”眼看大功即将告成,忽听一声马蹄响,归义军主将李少卿和他的胞弟李阳九赶了过来。
李少卿三十七八岁,长得虎背熊腰,但看他脸上气质却是文质彬彬如同一介书生。他的弟弟李阳九三十出头,身宽体重,一脸的大胡子,乍一看倒像比李少卿还大两岁。
李少卿大部走到浅水清面前,夺了了她手中的匕首,不知为何性情刚烈的浅水清在他面前显得异常温顺。
李阳九则掏出马鞭劈头给了祖冒两鞭子,将其叱退一旁。
李少卿将晴儿等人打量了一番,躬身施了一礼口称夫人,晴儿等人忙也还了礼。李少卿笑问浅水清:“舞跳了一半突然跑到这来,这是怎么回事?”
浅水清低着头道:“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话可说。请你放了她们。”
“我可以答应你,但你至少要给我一个理由吧。”李少卿说话的口气异常温柔。
“放她们出城,我跟你走。”浅水清平静地说道。
“这不算是一个理由。”李少卿摇了摇头,“你为何肯舍弃性命也要救她们。”
“她们的丈夫与我有恩,我不想欠她们什么。”
“恩,”李少卿点点头,“这个还算是个理由。好吧,我答应你,让福源长老带她们出城去。”
“你早看出来了?”浅水清被李少卿一语道破心中隐秘,既震惊又尴尬。
“这世上有什么事能瞒得过大哥?你一鼓捣大哥请福源长老来,大哥就猜中你的心思了,刚刚也是故意放你走的。”
听了这话,浅水清禁不住微微叹了一声,转身跪在晴儿面前道:“姐姐以后多保重了。”晴儿抓着她的手已是泪流满面。
祖冒挨了李阳九两鞭子,只过了片刻就忘了疼,凑上前暗问李阳九:“大将军把人放了,日后如何向曾重阳交代?”
“曾重阳就是个屁!”李阳九不屑地朝地上吐了口吐沫。
――――――
警一营的统军校尉吴波汉是刘毅峰的远房表情,靠着这层关系在原丰安刺史府混了个侍卫副领的差事,刘毅峰倒台后,他转投李通门下,李通行伍出身,看不上这种靠裙带关系上位的人,吴波汉在天德右军混的很不如意。杨昊改制时吴波汉走了庄云清的门路当上了由九娘关旧部整编而成的警一营统军校尉。从此吴波汉就被看做庄云清的人。
曾重阳也是这种看法,鉴于庄云清是韩遂的爱将,而韩遂与自己一直相处的很融洽,因此曾重阳自然而然地就将吴波汉也看做是自己人。在丰州各军轰轰烈烈的整肃运动中,警一营成了一块乐土。当其他营忙着互揭发、抓、杀王党余孽时,警一营的士卒却在忙着帮王默山的一矿挖土方。
王默山到底是个生意人,生意人立身处世的一条原则是永远不和当权者对着干,也永远不和当权者走的太近。正因为如此王默山的一矿才没有因为杨昊的突然倒台而受牵累。曾重阳从骨子里是看不起像王默山这样的商人,因此也就对他的这种转变不以为然了。当王默山带着一份厚礼来请王默山为他的煤矿改个名字时,曾重阳甚至都懒得见他。
与曾重阳的冷漠蔑视态度不同,庄云清对城南的这个煤矿倒显得很用心,只要有闲暇他就会带着丰安县的相关官员渡河去看看。说几句鼓励的话,然后尽醉而归。曾重阳知道这些,也派人暗中跟去查过,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
入冬后的连续雨雪让煤矿的工程暂时停了下来,大批的工人呆在工地上无所事事,年轻人天**动,常有三五成群的矿工渡河到城里来游玩。矿工活重,但收入不低,进城过后吃喝玩乐,银子流水价似的往外花,酒馆、客栈、曲舍、赌场的老板们乐的嘴都合不拢。
尽管曾重阳下有严令不得留宿矿工在城中过夜,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酒馆、赌场的老板们莫不是绞尽脑汁把人留下来。只要熟悉本地情况的县衙捕快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些外地来怛达人是想管也管不上。
一向以办事认真、执法严明著称的县令朱骧楠在这件事上却是不管不问,只要留宿城中的矿工们没有杀人放火,县衙的捕快们只当做没看见。
――――――――――
一场大雪过后,一矿被积雪压塌了两座工棚,上百工人无处居住。王默山向吴波汉求援,吴波汉禀明庄云清后让丰安城南巡防营让出几间营房给工人居住,腾出来的士卒则迁回城南的营地。
巡防营的一队士卒在通过丰安南门时突然被归义军巡检队拦住,硬说众人进城意图不轨,要将众人缴械带回营地讯问。巡城营士卒不肯缴械,双方顿时就冲突起来。巡防营人少,一动手就吃了亏。
警一营在城南营地驻有两哨人马,此时正在为河南迁回来的一队人腾营房。忽听那队人马跟怛达人在南门打起来了,而且吃了亏。当值的哨长顿时集结人马赶过去增援,两哨人马加上原先的一队二百多人打的巡检队丢盔弃甲。
吃了亏的巡检队立即派人向归义军城南守城使禀报,守城使一听火冒三丈顿时派三百人赶去增援。警一营士卒见势不妙向城西的铁铛营驻地退去。铁铛营是原天德右军的底子,战斗力远在警一营之上,只可惜此时主力驻在九娘关,营地里只有两队人。
当值哨长林英打开营门放警一营进来躲藏,然后命弓箭手守卫在营门前,下了死命令,谁敢通过下马桩立即射杀。
――――――
曾重阳得知城南之变时,林英已经射杀了归义军城南守城使摩歇心。摩歇心是李少卿胞弟李阳九的爱将,也是归义军的一员悍将。他骨子里看不起躲入铁铛营里的警一营士卒。所以当铁铛营的守门官警告他再向前就放箭时,摩歇心丝毫不放在心上。他骑着通体漆黑的“铁麒麟”洋洋得意地走过下马桩,营门后早就窝弓搭箭的弓箭手们顿时万箭齐发。摩歇心和他的“铁麒麟”被射成刺猬一般。
震惊之下的怛达人四散而逃,甚至连摩歇心的尸体也没人敢收。
“反了,反了。去,把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哨长给我抓来。”曾重阳捶着桌案冲朱七大喝道。
“是。”朱七阴着脸大步往外走。
“砰!”钦差公署大门被人一脚踹开,数十名怛达士卒手持弯刀冲了进来。
“闪开!闪开!”怛达人抬着一具人尸和一具马尸闯了进来。两具尸体上都插满了森森的羽箭。
“敢擅闯钦差公署,一律格杀勿论。”朱七一声断喝,数十锦衣侍卫从两边耳房里冲了出来将怛达人围了起来。与其同时公署大门也轰然关闭。
“且慢!”曾重阳一声断喝,忙从大堂内迎了出来。
“各位好弟兄,各位好朋友,稍安勿躁。”曾重阳堆起笑脸连连向归义军士卒弯腰打躬。
“我们将军冤死,你还能笑得出来,简直禽兽不如。”有人尖声叫道。
“胆敢侮辱钦差,给我拿下!”朱七一声喝,锦衣侍卫一拥而上将出言辱骂曾重阳的归义军士卒按在了地上。
“放肆!”曾重阳涨红了脸,大声吼道。三步做两步冲上前推开了锦衣侍卫,亲手扶起了满脸灰土的怛达士卒。那士卒没想到几个锦衣侍卫出手会这么快,这么狠,此时心里尚且砰砰乱跳。见了曾重阳竟说不出话来。
曾重阳一边替他拍打身上的尘土,一边不停地赔礼道歉。
“少在假惺惺!我问你,害死了我们将军,你打算怎么办?”
“啊,本堂一定会严惩凶手给各位好兄弟一个交代。”
“少打官腔。将军遗体就在这,你跪下来给他磕三个头。”
“使得,使得,死者为大。曾某理当如此。”曾重阳说着话弯腰就要跪,朱七上期一把搀住他,低声道:“大人,尊不跪贱。”
“哼,你懂什么!”曾重阳狠狠地甩开朱七的手,“尊者亦为逝者哀。”朱七闻听这话像被针扎一般,黯然地缩回了手。
曾重阳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朝摩歇心的尸体磕了三个头,正要起身却被怛达人拦住:“‘铁麒麟’与将军亲如兄弟,你给它也磕三个头。”
――――――
今天就这一更了,过年了嘛,俺也偷个小懒,休息,休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