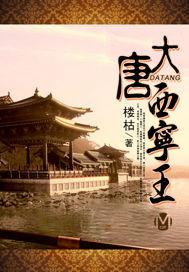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灵州,朔方节度使牙署。
刚从父亲手里接过朔方军政大权的王崇文,此刻内心焦躁异常。一个月前自己的父亲朔方节度使王希廉突然派他最信任的统军将军王东川将他从长安接回了灵州。王东川一路上没有对他透露任何消息,只是简单地说是自己的祖母病重想念自己。
王崇文知道这是个谎话,父亲王希廉有十七个儿女,王崇文排行老七,上面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虽说自己也是嫡出子女,但祖母唐氏的眼里只有自己的二哥、三哥才算的上是王家嫡脉,其他的子女跟王希廉收的几十个干儿子并没什么区别,不然又何以在自己十二岁时就把自己打发到长安,一待就是五年?
回到灵州后,王东川直接将他送进戒备森严的牙署,当见到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父亲时,王崇文才意识到自己今生恐怕再难回长安了。刚满五十岁的王希廉是在一次外出巡视时不慎落马摔伤的,因为伤口没处理好,回到灵州后便一病不起。重病中他听从自己老部下灵州刺史谢搏之的劝告,决定将朔方军政大权交给此前最不被看好的第四子王崇文。
为了杜绝自己死后朔方出现骨肉相残的惨剧,王希廉死前将自己的二子、三子、六子全部逐出灵州,又秘密处死了一批桀骜不驯的骄兵悍将。
在王东川和谢搏之的尽心辅助下,王崇文总算是站住了脚,但一场严峻的考验却不期而至。
“主公,密使来了。”谢搏之一个箭步跨进书房,见到王崇文一脸的紧张,安慰道:“主公不必担心,按我们议好的答复他,拿不定主意的,就拖一拖。这回是他们求我们,不必迁就他们。”王崇文点点头,整整衣袍迎到门口。
王东川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文士走了过来。此人名叫薄仲彦,做过一任长安县令,甘露之变后被革职回籍,后经吴臣举荐投在仇士良门下,甚为仇士良所倚重。
“在下此来一为恭贺少帅执掌朔方,二是带来了仇公的一封书信。”薄仲彦直抒来意。
王崇文颇为厌恶官场上的烦文缛礼,对薄仲彦的直截了当颇有好感。他接信在手却没有急着拆看,而是顺手将信放在了案几上。这让薄仲彦略微有些惊讶,他对眼前这个一个月前还是太学生的年轻人不由地多看了一眼。
“先生远道而来,请尝尝朔方的油茶。”
王崇文指着侍从刚刚送上来的一碗热腾腾的油茶说道。朔方与吐蕃接壤,双方虽交战多年,但民间往来一直不断,彼此都受到对方一些习俗的影响。
薄仲彦端起茶碗先是抿了一小口,接着又喝了一大口,细细品过,笑道:“这茶看着难看,喝着却别有风味。怪不得贵为公主也喜欢这一口呢。”
王崇文听到“公主”二字,脸色微微一变,继而笑道:“先生若是喜欢,学生就多备些让先生带上。”说着给一旁的侍者递个眼色。侍者刚要动身,薄仲彦喝了声:“慢。”
他目视王崇文,说道:“在下受仇中尉所托,请少帅出兵讨伐叛逆孟博昌、杨昊。”
王崇文冷笑了一声道:“先生若是带着圣旨来的,就请宣旨吧。”
薄仲彦冷笑一声,摇了摇头。
“既无圣旨,要我们出兵攻打天德军,只怕名不正言不顺吧?”王东川冷冷道。
“倘若仇中尉能帮少帅达成一件夙愿呢?”薄仲彦顿了下,提示道:“譬如奏请陛下将宜春公主许配少帅为妻。”
“仇中尉真的能办成此事?”王崇文听了这话,禁不住满面红光。
薄仲彦呵呵一笑:“如今天下还有仇公办不成的事吗?”
“给先生上杯香茶。”谢搏之说着话给王崇文递了个眼神,王崇文心里凛然一惊,自己太失态了。
“先生想必也知道,这几年老将军亲率朔方将士与吐蕃浴血混战,灵州城早已是兵困民穷,捉襟见肘,我这个刺史就像那无米穷妇伤透了脑筋哟。”
薄仲彦呵呵一笑,道:“朔方是大唐西北大门,风沙多油水少,刺史大人这个家确实不好当。此次少帅征讨逆贼,仇公愿助军饷白银五十万两。”谢搏之和王东川听到“五十万两”这四个字禁不住都是双眼冒光。
王崇文笑道:“多谢仇公美意,只是朔方乃是边镇,虽有数万精兵却要防备吐蕃寇边,只怕学生爱莫能助啊。”
薄仲彦道:“少帅所虑极是,若让朔方一家出兵北上平乱,势必迁延时日,给吐蕃以可趁之机。但若有夏绥、振武、河东三镇相助,平定孟杨之乱便易如反掌了。他日少帅大军入丰州时吐蕃人只怕还蒙在鼓里呢。”
王东川起身道:“主公,末将愿率朔方健儿北上平乱。”王崇文默默地点了点头。
谢搏之却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灵州银库是空了,不知仇公许诺的五十万两白银何时可以兑现?”
“三日后银车便到灵州。”薄仲彦答的异常干脆,反问王崇文:“不知少帅几时可以出兵?”
“三日后,五千先锋军便可沿河北上,十日后,王将军将亲率主力北上讨贼。”王崇文也答得很干脆,但他话锋一转:“但愿仇公不要忘了自己的承诺。”
“薄仲彦愿留在朔方为质,一个月后若见不到宜春公主殿下,不劳少帅动手,仲彦自裁谢罪。”
“好!传令击鼓聚将。”王崇文跳起身来满面红光地叫道。
――――――
延州,西风街。
华灯初上时,一个身穿黑斗篷的人敲开了福祥布庄的大门。
“对不住客官,小店打烊了。”小二揭开一块门板赔着笑脸说道,他正要关门,却被来人按住了手。
“一斤羊肉多少钱?”
“客官您走错地方了,这是布庄不卖羊肉。”
“一斤牛肉多少钱?”
“客官您走错地方了,这是布庄不卖牛肉。”
“两样加一起你总该卖了吧。”
小二嘿然一声冷笑,将来人让了进来。
“杀一个人,十天内办妥,这是定钱。”来人掏出一个鼓囊囊的钱袋子,将金条一根根摆在桌子上,金条黄灿灿的,在油灯下十分扎眼。但坐在他对面身穿蓝绸袍的中年汉子却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姓名?来历?住哪?”
“孟博昌、刺马营正三品横刀,住永丰;杨昊,刺马营从五品横刀,住永丰。”
“不接。”
“嫌钱少吗?”来人又取出一个钱袋子放在桌子上,袋子里是三颗夜明珠,价值是桌上金子的十倍。
“不接。”汉子丝毫不为所动。
“我劝你还是用骨牌奏报你们大当家。”来人丢下这句话便起身走了。
――――
东都洛阳城北的玉溪又称“君子河”,说起他的来历倒是十分有趣。这条穿城而过的小河大部呈南北走向,却在通明坊附近突然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变成了东西走向。若是不改向玉溪将穿过洛阳最繁华的两座市场,洛阳城中百姓都戏称玉溪是谦谦君子,宁可折腰也不愿沾染满身的铜臭味。
通明坊就位于玉溪的南侧,这是富贵人家的聚集区,高楼亭阁掩映在一片翠树名花中。而河的北则是贩夫走卒的杂居区,低矮破旧的房屋,曲曲仄仄的小巷,不要说外地人,就是在洛阳城住了一辈子的老客进去了也不免晕头转向,迷失了路径。
黄昏时分,一辆黑篷马车沿着玉溪河南岸的河滨小道进了通明坊北大门,停在了一座幽僻的府邸后门前,车厢里出来一个精干的年轻人,身上背着一个用小牛皮缝制的挎包。他四下打量无人后,几步跳上石阶敲开了大门。
年轻人是摩纱专门递送紧急文书的“跑马”,迎接他的是一名三旬出头的青衣管家,他仔细地检查了年轻人送来的公文包,确认封口金漆毫无破损后,便在年轻人递上的文牒上签了一个花押。
这份用油布紧紧包裹的公文包又经过了一连串的检视,最终落到了一双温润白皙近乎完美的女人手里。
这双手用一把精巧的小剪刀剪去公文袋封口的丝线,解开层层包裹的油纸,取出一摞用红绸绳捆扎的文牒,最上面的一张文牒上盖着一枚金印:骨牌急件!
这双手的主人没有资格去看里面的内容,她将文牒归档之后,取出那封盖着金印的文牒起身向锦屏后走去。锦屏之后挂着一道珠帘,珠帘内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美貌女子,她也有一双保养的很好的芊芊玉手。
她有资格看文牒里的内容,但没有资格做任何回答,于是她拿著文牒走出房间,顺着花廊来到了一座清幽雅致的后院。夜色来临,几名美貌的淡妆侍女正在院中点灯。
“属下有事禀奏。”美艳女子站在屋檐下轻声禀报。
“淑媛,你进来吧。”回答她的也是个女子,声音温柔动听。
“是。”淑媛应了声,轻轻地脱去鞋子掀开珠帘走了进去。
一股幽香扑面而来。正堂左侧室内,一名宫装女子正埋头拟写一份文稿,这女子不过二十出头,头梳宫髻,髻扎珠花,系一条浅黄色团花裙,外套红底黄色团花对襟阔袖长衫,唇点绛红,颐满目秀,面带微笑,矜持恬静。她的身侧跪着一个十五六岁的红裙少女,形容瘦小,体量未足,正专心致志地在剪烛花。
“明字门有一封紧急骨牌送到。”淑媛立在书案前轻轻说道。
“说些什么?”宫装女子仍旧写她的字,头也没抬一下。
“他们请示杀两个人?”淑媛顿了一下,补了一句,“是刺马营宝历社的两个人。”
“杀不杀谁,他们大当家不能定吗?这种事也要请示首座,分明就是推卸责任。”剪烛花的红裙少女忽然尖酸地插了一句。淑媛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你出去,我们有话要说。”宫装女子柔声说道,头仍旧没有抬。
红裙少女温顺地低下了头,背对着门慢慢地退了出去。
“这件事你怎么看?”宫装女子接过文牒看了一眼。
“茉莉说的也有道理,杀不杀谁,明门自己就可以定,为何要把骨牌发到这儿来呢?属下愚见,索性就打回去,让他们自己酌情处理。”
宫装少女略一思量,将文牒放在案头,“你先回去吧,容我先想一想。”
“是。”淑媛退出了房间。原本被赶出去的红衣少女茉莉又走了回来,依旧跪在桌案的右侧,她看宫装女子有些发呆,便说道:“把事情交给我,我帮你办妥。”
宫装女子笑了,她抚摸着茉莉柔嫩的脸问:“你打算怎么做?”
“我设法把消息告诉小鱼,让她去一趟永丰。”
“她一个弱女子能走多快?”
“她心里果真有哪个人,就会走的很快的。”茉莉拉起宫装女子的手放在自己脸上轻轻地搓揉着,喃喃地说:“若是为了紫宸姐,我也会走的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