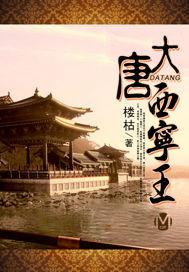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距离宜春公主下嫁小长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王崇文在流放地泸州病死了,
杨昊接到穆兰青从长安传來的密报时,他刚刚杀掉两个人,不是假手于人的那种,这次他亲手操刀,刀尖从皮肉刺进去,穿破肌肉,直达心脏,隋卧虎和隋鸢兄妹俩片刻之后,便魂归西方了,
此刻距离他们将杨昊出卖给文世茂整整五年整,这五年他们隐姓埋名,藏身在绛州乡下,以打猎务农为生,杨昊派去河东的特使颇费了一番工夫才将二人带回小长安,
隋卧虎自被擒后便一言不发,隋鸢却非笑即骂,面对杨昊狂笑不已,他的狂狷之态最终害了自己也害了隋卧虎,本來,杨昊是打断宽宥他们的,但面对隋鸢,他又改变了主意,
人杀了,仇报了,杨昊的心里却空落落的,挺难受,
这天是晴儿的生辰,吕芮一早在王芸儿处备办了一桌酒席,中午请晴儿去赴宴,晴儿被软禁在小长安郊外一座农庄,杨昊沒有派人监守她,只是跟她说若要离开小长安,务必來跟自己说一声,
晴儿一直沒有來找自己,他也从來沒有去找她,
本來是不打算过去的,不去虽然惦记,但去了可能会尴尬,
杨昊在大元帅府后衙大牢处决了隋氏兄妹后一时心里不痛快就决定回府去看看,走到半路想起吕芮今天又不在,回去也是无趣,便领着东方兰准备出城打猎,正在这个时候,收到了穆兰青发來的密信,
杨昊顿觉精神一震,当即决定去王芸儿那参加晴儿的生辰宴会,
他的突然到來彻底毁了寿宴,本來听说他不來,吕芮又邀请了宦妇名媛來凑热闹,鉴于晴儿现在尴尬的身份,多数年长持重的将军夫人都不愿來,來的都是年轻的姑娘媳妇,一大屋子人说说笑笑正受用,他这一來,除了吕芮所有人的拘谨起來,关楠、关梅两个吓得躲在晴儿身后,低着头不敢看他,
杨昊这才觉出自己來的太唐突了,但是既然來了,又不好就走,一时颇为尴尬,好在有吕芮解围,勉强说了几句话,敬了晴儿一杯寿酒,便匆匆忙忙地退了出來,
杨昊这无心之举,立即在小长安掀起一阵风暴,晴儿幽居的农庄顿时门庭若市,來看望送礼的车马络绎不绝,
晴儿不堪其扰,來求吕芮,请她帮忙给自己解围,
吕芮笑着说:“这样的事还不是越描越黑,你真怕她们打扰,不如搬进府來和我同住,这郡公府可不是谁想进就进的。”
晴儿苦笑说:“你说这话,我还不要羞死。”
吕芮说:“我劝你就不要端着了,你要是真跟他绝情绝义沒有瓜葛了,为何不带着关梅关楠走,别告诉我你一个弱女子沒办法,孟嫂子怎样,你这不是理由。”
晴儿道:“我跟你不一样,我拖着两个孩子呢。”
吕芮听这话寒了脸,说:“你这是笑话我是不能下蛋的母鸡咯,好容易背着公鸡出去一趟还沒能领俩鸡仔回來。”
晴儿脸腾地红了,急忙辩解说:“我哪有这个意思,你怎么能这么说,羞死人了……”
吕芮哈哈大笑,道:“我的好姐姐,你这么想就弱了,人家现在已经大彻大悟了,男女这点事,人家早看透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难过去了,再凑一对过夫妻有何不可,偏你死心眼看不透。”
晴儿听了这话红着脸低下來头,又说:“我怕他不能容俩孩子。”吕芮听了这话默然地叹了一声,说道:“姐姐你说,我们是不是都很沒用,跟着他那么久,怎么就一无所出呢,那些年他也是日夜耕耘,并不曾偷懒啊。”
眼看晴儿一张脸红的成了酱色,吕芮这才嘻嘻一笑,说:“行了,我看你今儿就搬进來吧,做西宁郡公府的秦孺人吧。”
晴儿道:“呸,我都不知道自个姓啥,你倒给我取了个姓,这算什么。”
吕芮道:“你别不知道好歹,孺人虽然算不得正妻,好歹也是有名有号在册有籍的,你让人家在宗籍簿上怎么记你的名字呢,晴儿,还是关夫人。”
晴儿发狠道:“吕芮,我知道你修成正果有资格欺负我了,可你别忘了我是什么人,欺我狠了,我宁可一死。”
吕芮说:“哟哟哟,用死來吓唬我啊,你怎知你死了,他就一定会处置我,他如今可不比先前了,滑头的狠呢,到时候他会想:哟,已经死了一个,我再弄死一个,就全沒啦,这买卖可不划算,罢了,死了就死了,是她沒福气,受不了我杨家的福气,弄口棺材厚葬了吧。”
晴儿的脸黑了,吕芮的玩笑也开够了,这才清了清嗓子说道:“你姓什么我不管,不过这进门的事,我可不能不操心,家里搁了条鱼,你看着守着,早晚还是得让他叼了去,索性洗洗煮煮让他吃了省心。”
晴儿道:“姓吕的,今天我不撕了你的嘴,我就姓秦。”
吕芮一边告饶,一边往外跑,跑到院中她便大叫起來:“瞧啊,秦孺人要打人啦。”
惹得仆役、丫鬟都來瞧热闹,这一下晴儿脸上挂不住了,躲在屋里把门栓死再也不露头,吕芮于是吩咐衣扬派人去把关楠关梅接來,划了一座院子给晴儿母子居住,对外就公然称晴儿做秦孺人,
一來二去,让杨昊知道了,他骂吕芮:“你这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你这样让她以后脸往哪搁,真是胡闹。”
吕芮翻嘴说:“别不知好歹,我这么做谁得利呀,她以后会不会丢脸,不在我,在你。”
杨昊气极而笑:“好你个吕芮,脑袋让门夹了吗,是你闹的满城风雨,怎么反倒是我的不是啦,你给我说清楚,说不明白,今晚别想吃饭。”
吕芮做鬼脸吐舌头说:“不吃就不吃,我到秦孺人那蹭饭去。”
杨昊冲过來就抓她,要打她屁股,吕芮就惊叫着绕着他转,两个人正在厮闹,晴儿突然闯了进來,寒着脸问二人:“你们把我圈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吕芮抢先一步说道:“本月十六就迎你过门,我们这正商量陪嫁呢。”然后她就跟杨昊说:“晴儿姐姐是自己人,用不着那些繁文缛节,我看能省就省吧,早日接进门才是正道。”
杨昊被她逼着,不得已只得应道:“啊,那不好吧……“
晴儿冷冷地说:“那当然不好,如今我是守寡的寡妇,要再嫁人,必得有媒聘之仪,否则我宁可死,也不过你杨家门。”
晴儿寒着脸说完,扭头去了,
吕芮急了,挥舞着两个小拳头朝杨昊嚷道:“我也要有媒聘之仪三媒九聘,一样不能少。”
杨昊提醒她道:“可是你已经进门了。”
吕芮道:“那也不行。”
随即就哭丧着脸说:“我怎么就那么傻,稀里糊涂就进了你的门。”
晴儿当晚搬出郡公府,七日后以寡妇的身份再嫁进來,杨昊给她取了个正式的名字秦晴,杨昊对自己的得意之作颇为得意,一连几天围着晴儿叫亲亲,直到长安城传來李晴要以妻子的身份去泸州为王崇文奔丧的消息,
杨昊一时说不出话來,从礼制上说,她现在还是王崇文的妻子,妻子为丈夫奔丧也算天经地义,
杨昊有些恨李炎和仇士良,明明是已经答应自己的事,为何不办的干脆利索点,王崇文现在是待罪之身,一纸诏书,或稍加暗示,自然会有人站出來为李晴说话,要他们离婚,什么礼法、名誉,话不还在你们怎么说吗,
不过现在还不算晚,一位公主出京为丈夫奔丧,可不像寻常百姓家,有许多麻烦事要做,如果那个环节出了问題,她的一腔愧意也只能在她长安的府邸里发发了,
杨昊赶紧给唐虎写信,请他务必去见李晴一面,是为了安抚,也是为了开导,希望李晴能在伤心之余,还想想自己,想想在长安的西北还有个人在期盼她的到來,
唐虎现在在刺马院挂一个空名,领一份俸禄,早已不上院当差了,因为他是个散淡的人,又是个行将就木的糟老头子,看管李晴的吴臣对他网开一面,允许他时不时地去探望一下这位被幽禁的公主,
新皇登基后,他甚至可以直接进入公主的府邸,而不再需要吴臣手令,
接到杨昊的信,他问老妻:“你说我该拿一张笑脸去见她,还是苦着脸去见她。”
老妻笑道:“顺其自然就好。”
李晴是十天前从李好古那知道王崇文病故的消息的,李好古是自她被张海劫持到长安后,唯一能见到的宫里人,文宗皇帝驾崩,李好古立即改换门庭,成了大太监刘弘逸的得意门生,不仅在新皇帝面前得宠,仇士良也把许多隐秘的事交给他來办,一时在宫中竟混的风生水起,
这日,李好古奉新皇之名给李晴送了一盒子薯饼,李晴又逼着他把王崇文在泸州病逝的前后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她倒不是闲极无聊,而是想知道李好古的话里有沒有假,假话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说着说着也就露底了,
李好古详详细细地把王崇文怎么离京,怎么行路,到了泸州后怎么感染风寒,请的什么郎中,用的什么药,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跟上回说的一字不差,李晴失魂落魄地听完,立即又泪流满面,这个跟自己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自己既厌恶又可怜的人,活着时形同陌路,死了才突然知道他原來一直在自己的心里占有一席之地,只是位置太偏,一直忽视罢了,
李晴努力地回想起他和自己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记忆里的东西实在太少了,能回忆的东西实在是不多,
她哭了一阵,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等她意识到李好古仍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时,心头莫名冒出一股无名火,她冷笑道:“这下你们满意了吧,母亲早不在了,父亲又遁入空门,太皇太后又不管我,如今连挂名的丈夫也沒了,你们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吧。”
李好古道:“人死不能复生,请公主节哀。”
李晴含泪道:“我还要节哀做什么,与其孤苦伶仃一个活在这无情无义的世上,不如死了干净。”
“哎哟,您这话说出來,可要伤了一位好人的心了,为了您,人家可沒少下本钱。”
“本钱,我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能值多少钱。”
“瞧,奴婢这张臭嘴,该打,该打。”李好古装模做样地扇了自己两个嘴巴子,
“公主啊,不是老奴多嘴,您与王崇文缘分已尽,这是天意,这是上天对您这么多年受的苦的报答,公主啊,您要伤心就哭上几嗓子,哭完了您还得高高兴兴地嫁人呢。”
“嫁人。”
“可不是嘛,自打开春起宫里就忙着为您准备嫁妆啦,您是当今天子的妹妹,您未來的夫君是雄镇西北的兵马大元帅,当朝一品,哪敢敷衍呢。”
“把我卖给他,你们赚了不少吧。”李晴出言讥讽道,
“且不论赚多赚少,老奴斗胆问公主您一句:您心里就真的不想嫁给他吗。”
李晴吐了口气,沒说话,
“您不说话,那您就是默认啦,唉,要说公主您呐是最英明睿智不过的,‘易得无价宝,难觅有情郎,’戏文里不就这么唱的吗,如今好事让您撞上了,您还折腾什么呢,您若真觉得对王崇文有一份愧疚,就在长安为他设个牌位,每日为他念经祈福便了,又何必要跑去泸州呢,那样做,真能让您心里安宁,老奴看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好,你个老奴才,你信不信我问皇帝要了你。”
“信,您呀最好要了老奴,以后想打便打想骂就骂,老奴知道公主您再怎么打骂奴婢,也不会取了老奴的性命,老奴或许就能得善终了。”
李好古说着说着就跪了下去,挤出了两行清泪,哭的煞是伤心,
“要不要你,我还要思量思量,你起來吧。”
李好古道了声谢,抹着眼泪说:“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大行皇帝走了,老奴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莫看现下还活得像个人样,说不得一眨眼的工夫就身首异处了呢,老奴的话请公主务必记在心上,只要公主为老奴说句话,老奴的性命就保住了。”
李晴不觉有些心软,就说:“你起來吧,只要我还能见到皇兄,我一定为你说话。”
李好古大喜,说:“能的,能的,皇帝迟早是要召见您的。”
李晴淡淡地说:“但愿吧。”
她一回头看见唐虎正站在门口,捻着须望着她笑,李晴招呼了一声:“先生你來啦。”
李好古吓了一大跳,唐虎上前來给李晴行礼,李晴忙扶住说:“先生不必多礼了。”
唐虎说:“君臣有别,平日私下里老夫倚老卖老装糊涂,今日李公公可在场啊。”
李好古说:“哟,老先生您这一句话可把我压的万劫不复啊,朝廷尊重老臣,礼制上也有定规,三品以上官员见了亲王公主是不必下拜的,我若沒记错的话,您的头上可顶着检校兵部尚书的官呢,三品高官呐。”
唐虎笑道:“我这个三品,可比不上公公您这六品实惠啊。”
李好古说:“要不咱们换换,你进宫当差,我去刺马院享清福。”
李晴说:“老先生你不要跟他嚼舌头,他们这些人整日在宫里就指这个过日子,你纵然胜过他,也惹了一声骚。”
李好古说:“行啦,我走,唐尚书您陪公主说话吧。”
李好古一摇三摆地走了,唐虎望着他的背影笑道:“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投在刘弘逸门下,你看他比在先帝驾前还风光呢。”
李晴笑道:“他刚刚还哭着要投到我门下呢。”
侍女送上茶水,唐虎一面喝茶一面问道:
“哦,那公主答应了吗。”
“我不知道,答不答应还不得他说了算嘛。”
唐虎放下茶碗,说:“依我看,公主不妨答应下來,李好古在宫里待了这么多年,他的肚子里可藏着一本宫廷秘笈呢。”
“我倒是希望这本秘笈毁了的好。”
“毁不得,毁不得,树欲静而风不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李晴默默地点点头,说:“我懂了,谢谢先生指点。”
唐虎道:“眼看就要到六月了,殿下真的要去泸州吗。”
“我想去泸州为他守孝三年,以宽恕我心中的罪孽。”
“三年时间太长了,古人有守孝三年之说,但庄子也有言云等我的坟干了你就可以去嫁人嘛。”
李晴红着脸道:“先生无缘无故的为何要笑话我。”
唐虎道:“不敢,不敢,我只是想礼法,名誉啊,这些东西本就是虚无缥缈的,有也可,无也可,公主觉得对王崇文有愧,可是,真为他守孝就能减轻您内心的负疚吗,我以为与其在泸州筑庐为他守孝三年,不如为他洗清名誉,让他叶落归根,若有余力再收拢王家旧族,这样才是真正对的起他,才能真正减轻负疚之心。”
李晴大喜道:“先生一席话真是点醒了我,我要请皇兄为他洗清罪名,还他清白。”
谈空道:“公主有这份心便可,事嘛,一步步來,不着急。”
李晴说:“那可不行,他要是不答应我就去泸州守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