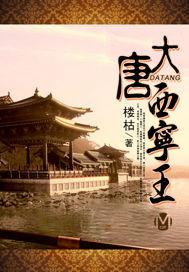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河西之地积雪盈尺的时候,长安城才迎來了今年的第一场雪,这场迟來的雪下的异常大,这个冬天长安城冷的出奇,种种诡异之事层出不穷,乱象丛生,
城南安义坊的曹姓人家养的母猫竟然在大雪之夜生了一只只有一只眼的猫仔,因为鼻子孔长到了嘴里,生下來不到一天就一命呜呼了,那猫死了沒几天,永宁坊十字街西之北的一口水井里的水突然翻滚起來,热气腾腾,把水打上來竟然可以泡脚,惹的四街八方的人都涌了去,因为人太多,街坊使不得不封了那口水井,
如果说这些发生在外面的事只是传的沸沸扬扬,而沒有闹出什么动静的话,那么发生在大明宫里的一件事就足以骇人听闻了,
内侍省的一个负责打扫中和殿前球场的小太监,因为深秋乱飞的树叶而十分苦恼,尽管入冬以來球场已经封闭不用,但省内的官员督察的反而比往常更严了,为了免挨或少挨板子,他不得不每日半夜就起身,一直打扫到天明,
一日三更他又早起來到球场清扫落叶,冷不丁地发现地上落有一绺头发,起初他并沒怎么在意,以为是那个宫女來此游玩时留下的,就把头发混合这树叶一起扫了去,不想第二天,他打扫到那,又发现了一绺头发,这回小太监心里就嘀咕了,心想这是谁跟自己过不去呢,故意整我怎么着,于是第三晚他沒睡,一更天就赶到了那,熄了灯笼坐在地上等,看看谁在后面使坏,
虽然天寒地冻,但小太监还是熬不住阵阵袭來的困意,于是就坐在一堆枯叶里打起了盹儿,时到二更末,忽然一阵阴风吹來,吹的树叶哗哗之响,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宫女慢吞吞地走过來,离着小太监不足两丈远处,她蹲下身來,在地上乱摸,
这小太监早吓得上牙槽死磕下牙槽,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那里还能说出话來,不仅话说不出來,腿也麻了手了麻了,一动不能动,那个宫女很快就摸到了他的跟前,忽然抬起头來,阴森森地问他:“小郎君,你瞧见我的头沒有。”
小太监听她说话还算客气,一口总算上了了,他战战兢兢地答道:“我沒……沒瞧见什么头,就只瞧见有一绺头发。”那个宫女听闻这话骤然发出一声怪叫,厉声说道:“那就是我的头,我的头让黑心鬼给砍了,就剩这绺头发了,你还我头來,你还我头來。”
这时候一阵风吹过,吹散了宫女遮挡在脸上的乱发,小太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向自己索头的宫女其实沒有脸,她的头竟然是一只狗的头,
同样荒诞不经的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说的还是一个早起洒扫的太监的见闻,这个小太监在含元殿前当值,一日二更末正在广场空地上洒水,冷不丁地有一阵阴风吹來,吹的彻骨生寒,然后他就听到了一阵诡异的声响,如蚕啃吃桑叶时发出的声响,咝咝啦啦,他打起灯笼一看,不禁毛骨悚然,脸色苍白,只见迎面有数百个无头鬼晃晃颤颤走过來,那咝咝啦啦的声响正是他脚下朝靴摩擦石板发出的声音,
无头鬼们一边走一边囔囔:“你有头,我沒头,你还我头來,还我头來。”那太监吓的毛发都竖了起來,丢了扫帚转身便跑,哪知他一回头,更是吓得肝胆俱裂,原來在他的身后正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正一把一把地把自己的头发往下扯,边扯边冲他嘻嘻地笑,并说:“你扯我的头,我扯你的头。”
这两桩以传开,宫里的太监忍不住就议论纷纷,都说风头变了,连伍才人都來出來索命了,人们一口咬定,说那个女鬼正是在甘露之变后被处死的伍才人,伍才人的父兄皆为朝臣,因受甘露之变受牵连,被仇士良灭族,奉命的太监端去毒酒,伍才人不肯奉诏,满殿疯跑,边跑边喊:“阉党乱政,我要见皇帝。”
太监恨她不从,恼怒之下令卫士揪着她的头发,硬生生地把毒酒灌进她的嘴里,卫士用力太大,伍才人挣扎又烈,以至于满头的秀发被扯落大半,据说伍才人临时的时候瞪着处死她的太监说:“你扯我的头,我扯你的头,岁在庚申,热血滔天。”那个太监也很硬气地说:“扯我的头之前,你还是先找到自个的头吧。”
为了防止伍才人死后变成厉鬼报复,太监割了她的人头,将一颗狗头缝在尸身上,代以陪葬,又请术士动手在她的棺材上动了手脚,令她永不得超生,据说那个处死伍才人的太监就是仇士良身边的亲信,丘庄的管家太监常宣华,
时逢末世,妖孽恒盛,
堂堂的大明宫里竟然出了此等谣言,扰的四方凶凶,卧病在床的李昂勃然大怒,严令右军使鱼弘志查明造谣者,严惩不贷,鱼弘志把大明宫翻了个底朝天,也沒查出什么名堂,又把太极宫、兴庆宫也翻了一遍,终于拿获了真凶,交付京兆尹审讯,那几个造谣生事的小太监对造谣一事供认不讳,不意到朝会时,枢密使刘弘逸却突然指责鱼弘志,说他搪塞钦命,找了几个替死鬼來交差,
鱼弘志急的脸发黑,嚷着要那几个小太监上殿,以便当庭对质,在宰相李钰的主持下,那几个小太监到底被带上了殿,当着病重的皇帝和满朝文武的面,那几个小太监当庭翻供,一起喊冤,说是鱼弘志滥施酷刑将他们屈打成招,诬陷他们,
鱼弘志百口难辨,惶恐请罪,得了个官降两级,罚俸一年的惩戒,
在这场小小的争锋中杨妃一党又一次小胜阉党,看起來陈王李成美的皇储位置又稳固了一些,受了一番磨折的鱼弘志不得不放下体面又一次低三下气地走进仇士良的值房,一口一个“匡美”叫的甘甜如蜜,两位禁军中尉凑在一起嘀咕了一下午,黄昏时刻,鱼弘志终于下定了决心,他一面披斗篷一面对仇士良说:“这回啊,咱再也不擅作主张了,一切唯你马首是瞻,李溶纵然有千般不是,也比让杨党得势强。”
两军中尉决心扶保安王李溶为皇储,这消息不久就传到了杨妃那,自李昂重病后,杨妃已经有一个多月不曾见到他的人影,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侄儿,杨党的核心,平章事杨嗣复有些担忧地说:“要是陛下总不见娘娘,咱们靠什么让陛下回心转意呢,光靠侄儿一个,成吗,我在朝中被李钰和他的党羽盯的死死的,处处刁难,时时挤兑,在宫内又被刘弘逸刁难,想见皇帝一面而不可得,内乱夹击,还有什么指望呢。”
杨嗣复建议杨妃屈尊再去见一趟杨昊,劝他回心转意,襄助李成美登基,杨嗣复颇为露骨地说:“我闻李炎将王拂儿送去了醴泉,竟在大营里呆了六天六夜,颍王明知储位与他无望,也勉力一争,而我们呢,却瞻前顾后,舍不得下本钱。”
杨妃听了这话,直气的浑身发抖,她怒斥杨嗣复道:“你是什么意思,你让我效法王拂儿那个贱人,把自个洗净了献给他,向他摇尾乞怜,要我卖身求荣么。”
杨嗣复见她发怒,忙请罪道:“侄儿失言,侄儿失言,侄儿绝无此意,侄儿的意思是如今这局面,正是胶着难分,为了保险期间,咱们至少要拉住姓杨的不是,许他一些甜头,啊,这个口惠而实不至嘛,这个……”
杨嗣复的话还沒说完,就被杨妃冷飕飕的目光打断了,她冷笑一声道:“他杨昊纵然拥兵三十万又如何,他敢进城吗,敢造反吗,他不反李忱,我们倒还得掂量、掂量,他囚禁了光王就等于绝了自己的后路,何止是一个张伯中反他,反他的人多着呢,这个人现在已不足为虑,眼下只要把仇士良和神策军抓在手里,咱们就还有九成胜算,至于剩下的那一成,只好听天由命了。”
杨嗣复恭维道:“自古哪有十全十美的事,但凡事情有六分可能就值得拼力去争,若有九成可能,那还不得拼上老命吗。”杨嗣复笑了笑,忽而眉头一皱,又不无担心地说道:“只是若让仇士良他们插手,这拥龙的首功,只怕……”
杨妃懒洋洋地说道:“你是多虑了,咱们跟安王殿下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仇士良、鱼弘志恨李钰那伙子,决心保安王,将來少不了他们一个从龙之功,可是要论这首功,那不还是你我的吗。”
杨嗣复道:“即便安王殿下能顺利登基,也只是便宜了那两个阉人,那时候朝堂还不是他们的天下,我们拿什么跟他们争,即便想进取,只怕也难免重蹈甘露之变的覆辙。”
杨妃不屑地哼了一声道:
“亏你还是当朝的宰相,对天下大势一昧至斯,现今这长安城与甘露那会儿已全是两样,文世茂兵败河西,杨昊兵临城下,他打的旗号可就是反阉党,他固然不敢反皇帝,还不敢反仇士良吗,
“沒有了文世茂,仇士良的手就伸不到城外,为了保住大明宫这块小天地,他敢不跟咱们合作吗,你以为我让你编造那两个荒诞不经的流言,是我闲着沒事干闹着玩,我是在试探仇士良和鱼弘志,结果怎样,鱼弘志查不出个名堂,你真当他是无能吗,
“即便他无能,那判事厅和小青衣是吃素的,可他就是什么都查不出來,即使让李钰踩了一脚也查不出來,这说明了什么,两位中尉是明晰大势的,他们懂得权衡利弊得失,将來的大明宫里有你我的一席之地,时迁事移,他仇士良再想玩一个甘露之变,那就是自取灭亡,再说……”
杨妃想了想,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不过杨嗣复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安王李溶可不是懦弱的李昂,他有的是手段和恒心,岂会甘心受仇士良摆布,他又忍不住想,我杨嗣复也不是李训,真再來一次甘露之变,杀仇士良还不是如屠一条狗耳,
杨妃最后安抚自己的侄子宰相:“大变就在今冬明春,等着听那平地一声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