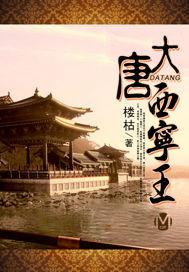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武曹、顾神火、李秀元接余炎炉入关,即便将兵权拱手想让,奉余炎炉为主将,余炎炉好言抚慰了顾神火,对三人道:“庆州城破就在今晚,王艺败军必然向这來,到时诸位务必扎紧口袋,只要坚守两天一夜,便是大功一件。”
武曹道:“重字关北面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守两天一夜不难,怕只怕南面,若余澄倾城而來,未必能守的住。”
余炎炉道:“无妨,我此來带的都是骑兵,我准备列营关下,他若來,不待他靠近关隘,我便冲他个七零八落,几个残兵败将,还能攻城破关吗。”
三人大喜,当下分配了顾神火率所部八百人守北关,武曹、李秀元所部居中策应,烈火营屯驻关南,防御南方來敌,
刘盘一声令下,庆州城就镀了个金边,从高处活像戴了一个大火圈,孟明攻西城、刘丰攻北门,一时杀声大作,王艺久在边关,这等阵势早已见怪不怪,在城头督战至深夜,见攻城之敌陆续退去休整,老将军遂起身來,伸个拦腰,对身边诸将说:“刘盘小儿用的是疲敌之计,咱们不上当,留两成人马守在城头,其余的回去歇着,养足了精神才能跟这帮小子耗下去嘛。”
他提着钢刀,沿着城墙巡视了一番,便回到中军,卸下盔甲,正拿热水泡脚,冷不丁听到外面鼓声大作,眉头一皱,暗骂道:“这帮兔崽子,半夜也不让消停,敲敲敲,敲破你娘的棺材板,老子也不出去。”
老爷子稳坐中军帐,其子王澜却蓬头垢面地跑了进來,边跑边喊:“爹,爹,爹,鞑子攻城了,攻势凶猛,怕是要守不住了。”
王艺喝道:“放屁,再敢胡言乱语我砍你脑袋。”
王澜一缩脑袋,不敢吭声了,却暗中向身边一个校尉努了努嘴,那校尉禀报道:“大帅,标下刚刚巡城路过巡城营,见营里加强了戒备,似有异动,标下请示,是否派人去探个明白。”王澜附和道:“要去,要去,李休得部离北门最近,北门有失,城就保不住了。”
这话说的王艺心里一紧,前两天李休得曾劝过他出城归降杨昊,他说杨昊是朝廷钦命的总统漠北河西振武节制五军兵马大元帅,此番南下是奉旨讨伐阉党,身为大唐臣子,岂能抗命保阉,‘
李休得是王艺的义子,也是王艺看着长大的,一向对自己忠心耿耿,王艺听了他这番话,不仅沒有责怪,反而赞他有忠君之心,他对李休得说:“你有一腔忠义是好的,但你到底还是太年轻了,谁是忠,谁是奸,谁來定,你说忠于天子是忠,他杨昊说自己忠于天子,仇士良也说自己忠于天子,看起來都是忠臣嘛,两个忠臣打起來,天子尚沒说话,你着急什么。”
李休得道:“阉党荼毒天下,世人皆知,打阉党的自然是忠臣。”
王艺笑道:“岂不闻狗咬狗一嘴毛,坏人和坏人也能打起來嘛,贼和贼因为分赃不均,不也常常火拼嘛,你能说那打贼的就是好人,杨昊本是公卿之后,因为甘露的事儿受了牵累,一怒之下逃到边地,割据称王,被文公剿灭后,竟然跑到漠北,入了契丹籍,变成了个契丹人,你说这样一个人他能是个忠臣吗,他那个总统、节制九成九是他自己封的,他说手里有讨伐阉党的密旨,你看到啦,他要跟仇士良斗,自有他的目的,咱们看着就是,所谓成王败寇,等他胜了再说吧。”
李休得听了这话方诺诺而退,
王艺此刻嘀咕:我这话已经说的十分明白,这小子也不是糊涂蛋,怎么就听不进去呢,难道是杨昊许了他什么好处,嗨,这个糊涂蛋,他许你再大的好处,能有老子给你的多吗,
王澜见父亲皱眉不语,催促道:“李休得若反了,城就沒了,爹,不可不慎啊。”
王艺喝道:“胡说,大敌当前,加强戒备有何不妥,怎么就成了不轨之心,再敢妖言惑众,我定不饶你。”
王澜被他这一骂,怏怏地说道:“左右孩儿也帮衬不了什么,爹,容儿子去见见祖母,兵荒马乱的别吓着老人家。”王艺的母亲刘氏这年七十七,住在城西一处偏僻宅子里,王艺奉亲至孝,闻听这话,脸色稍缓,就哼了一声,喝道:“要去就去,啰嗦什么。”
王澜骑马來到城西一座偏僻的宅子门前,敲了三下门环,一个三角眼的小厮探出头來,问道:“三爷,老爷子答应了吗。”
王澜道:“沒答应,不管他了,我这个做儿子的该说的都说了,仁至义尽了。”
他随小厮來到内院,房厅柱子上捆着一个身穿甲胄的年轻校尉,年轻人的嘴被一团烂布塞住,眼也被蒙上,王澜撤下他的眼罩,年轻人见了王澜恨的双眼冒火,若不是被绳子捆着早窜上來啃他几口了,
几个小厮护主心切,早拳脚俱下,打的校尉眼泪直流,
王澜喝道:“都给我住手,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哦,还不是将军,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当上将军的。”看那年轻人稍稍消停一些,王澜拽出他嘴里的烂布,年轻人呼呼地喘了两口气,喝道:“你这个蠢蛋,你要干什么啊。”
这个年轻校尉就是李休得,昨晚奉命巡城时被王澜拦住,强拉着他去喝酒,李休得本不愿去,耐不得他拖住不放,当着下属的面也不好太驳王澜的面子,就随他进了一家酒楼,几杯酒下肚,不知不觉就头昏眼花,昏死过去,等醒來就发现自己手脚被捆,嘴被塞住,眼被蒙住,他战战兢兢过了大半夜,以为自己得罪了什么人,要遭报应了呢,
谁曾想抓自己的竟然是王大傻子,
王澜笑道:“你不要急,听我慢慢说,我知道你是老爷子的好义子,可你别忘了,我是他的亲生儿子,老爷子年纪大了,脑瓜子有些不好使,眼见得荣华富贵就在眼前也不知道去取,荣华富贵不取倒也罢了,可要是闹个谋逆大罪,株连九族,那就是悔之晚矣啊,大哥、二哥不在了,我是家里的独苗啊,别人不操心,我不能不为王家着想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呢,我打算和老弟一起兵谏,劝老爷子打开城门,迎接杨大帅进城,咱们合兵一处,杀奔长安,屠尽阉贼。”
李休得怒道:“愚蠢至极,愚蠢至极,凭你的糨糊脑袋,能想什么事,你还想做忠臣,我看你弄不好要死无葬身之地,遗臭万年,你赶快把我放了,我只当这件事沒发生过,你是我义父的独子我能把你怎么样。”
王澜冷笑道:“兄弟,我好心好意,你全当驴肝肺啊,那就别怪兄弟无情了。”
李休得冷笑道:“你要杀便杀,老子眨下眼,不算是好汉。”
“杀你。”王澜怪笑道,“那是太便宜了你,实话跟你说吧,我已经跟老头子说了,说你打开北门投敌去了,你说老爷子怎么说,‘忘恩负义的东西,我要杀他全家’,嘿嘿,他老人家要杀你全家咧,我这边跟老爷子说了,那边又去告诉你的那些结义弟兄,你猜我怎么说的,我说啊:你们大哥劝老爷子投诚,老爷子不乐意,一刀把你们大哥宰了,你猜他们什么反应,嘿,一个个都跳了起來,群情激奋啊,我又跟他们说:老爷子糊涂了,我也沒办法,劝不住啊,哥几个,我跟休得不是一个爹妈,可胜过亲兄弟啊,哥不忍你们受戮,嘿,你说我这个词说的多好,受戮,比说被杀好听多了。”
李休得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來了,他哈哈大笑,笑的眼泪都出來了,
王澜对几个无赖说:“你们看,他乐的笑了,嘿,大哥这手段怎么样。”
众人附和道:“妙计,妙计。”
一个尖下巴的瘦子眨巴眨巴眼,小心地问道:“可是大哥,兄弟们听了半天还是沒弄明白,您这是唱的哪出啊,逼反了巡城营,对您有什么好处呢,老爷子要是丢了城,您也沾不到便宜不是。”
王澜道:“你们这些人就是家家亲亲,岂不闻……”他翻了翻白眼,想不出词來,就强词夺理地说:“为人臣子心里哪能光装着自个呢,要装着陛下,装着社稷,装着天下苍生,老爷子糊涂了,我们也能跟着糊涂吗。”
李休得哭笑不得地说道:“你这个王大傻子,你算是把老爷子害死了。”他猛地一挣,怒喝道:“你把老爷子给害死啦。”
王澜望着他势若疯虎的架势,心里一咯噔:我真把老爷子给害啦,
城外鼓声越來越响,杀声越來越大,加之儿子王澜那番言辞挑唆,老将王艺在后帐坐不住了,于是传令升帐,诸将皆在,惟缺李休得,王艺心中更疑,问中护军:“李休得何在。”中护军答:“巡城营说李休得昨夜掌灯时出营巡视,至今未归。”
王艺怒道:“混账,主将出营不归副将为何不报,
巡城营副将连忙出班报道:“李校尉一向严谨,今日不知何故未归,属下已派人出去寻找了。”王艺道:“等你们找到我这城怕也姓杨了。”喝道:“将这厮拿下。”令:“左右营何在,立即将巡城营围住,让他交出兵器,违者斩。”
左右两营将官领了军令,尚未出门,便有飞报:巡城营反了,
庆州城在拂晓时分陷落,王艺率残部万人退至重字关下,关门紧闭不得入内,刘盘、孟明挥大军急速杀到,王艺无奈,令大军依关布阵,决心与敌决一死战,副将胡玉劝他:“腹背受敌,兵家大忌,大帅不为自己也该为万名将士留条生路。”
王艺道:“我一生忠于国家,到死了还要做个叛臣吗。”他对胡玉说:“你拿我的人头去求降吧。”
王艺想死却沒能死成,胡玉等将领抱住他,夺了他的剑,下马去向刘盘投诚,刘盘望着须发皆白的老将,说道:“你明知儿子不肖,不肯重用,这是你的精明,可惜啊,都说知子莫若父,你却不知你的儿子原本是个人才啊。”
刘盘让已经归顺的王澜出列相见,王澜见他父亲吓的肝胆俱裂,颤抖着不能吭声,王艺蓦然大吼一声一头扑了过去,用手卡着王澜的脖子,如疯虎般怒吼不歇,等卫士掰开他的手,王澜已让他活活给掐死了,
直到庆州城陷落的第三天,余澄才统着邠宁镇的主力由宁州來救援,出城三十里就遇到刘盘的主力,双方打了一场面对面的野战,仗打到一半,余澄就撤回了城里,出城时一万五千人,回城不足千人,余部半数被歼灭,半数投诚,还有少许逃入深山,
大军抵至城下,余澄明知不敌,放了把火就望南窜去了,刘盘紧追不舍,余澄逃到邠州城下,守将见敌势太大,竟闭门不纳,余澄只得绕城逃往岐州,刘盘围住邠州,劝守将投降,守将不愿叛国,也不愿与刘盘为敌,遂达成协议,刘盘开城南一门,任守军退出,兵不血刃地占据了邠宁,
刘盘志得意满,喜气洋洋地对羊弘扬说:“西南百里便是长安,说什么虎踞龙盘,竟是入无人之境,你说这神策军都死绝了吗。”
羊弘扬道:“大将军奉旨讨伐阉贼,随乎天意,合乎民心,自然无往而不胜。”
刘盘大笑,用马鞭向西南一指:“十日内我必拿下长安。”
羊弘扬劝道:“将军南下只为攻取邠宁,如今大功已成,下一步何去何从,该听大帅指示,各军若不能协同,纵然打下了长安,只怕也不能守的长久。”
刘盘在羊弘扬肩上一拍,笑道:“这个道理,我岂不知道,说笑而已。”即令军中掌书记:“即刻行文给大帅,请指示下步方略。”
此次南征不到十天,就拿下了邠宁三州,距西北而窥长安,胜利來的太快,反倒让杨昊心里沒了底,不是说文世茂已经领衔出征了吗,怎么一路行去不见一个人影呢,就算他用兵奇诡,数十万大军何处遁形,长安的西北大门又岂敢弄险让人,
深夜了,他还端着烛台在沙盘前徘徊,想破了脑袋终究一无所获,
怪哉,怪哉,这个文世茂,当真是深不可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