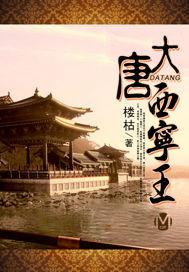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有了乌隗人做靠山,小仓山的境地由四面受敌的窘境变得八方逢源的顺境,压力一减,杨昊骤然间肥胖起來,起初他还沒注意,直到有一天,他和杨欣在床上翻云覆雨时,杨欣忽然睁开眼,双手托着他的身体,哀求地说:“喘不过气了。”
杨昊像被蛇咬了一样,赶紧离开杨欣的身体,杨欣娇羞地赶紧拉起被子盖住自己,神态慌乱的仍如初夜一刻,杨昊恶作剧似的拉去薄被,杨欣的身体坦露无遗,白发发,肥嫩嫩的一团,经过大半年的滋养,初來时的黑瘦孱弱变得白嫩鲜活起來,在床上与杨昊的合作也日渐谐和起來,只是交接时仍不肯睁开眼,这一半出于她的羞怯本性,另一半也源于乌隗部的一个隐秘传说,
话说男女交媾是颇费精神的事,交媾太多则易短寿,为了涵养精神、延年益寿,最好少上床,实在忍耐不住时,便最好闭着眼,免得心神外泄,最好咬着牙不啃声,免得精元丢失,这些道理在杨欣出嫁前母亲跟她说过,自己的姐姐也特意关照过,当这个陌生男人躺在她身边时,她一度也羞的睁不开眼,抬不起头來,这个男人除了满身的酒气之外还有一股热烘烘的汗臭味,这些气味刺激着她的鼻孔,她的心也随之剧烈地跳动着,如同怀揣了一只淘气的小鹿,
那个男人终于坐在了自己的身边,他的气息清晰可闻,他就在那盯着自己看,杨欣把双腿夹的铁紧,抄在袖子里的手握住了匕首的手柄,那是一柄闪耀着蓝莹莹的光芒的匕首,削铁如泥,自六岁生日那天父亲作为礼物送给自己之后,就一直随身携带从未离开过半步,即使睡觉也放在枕头边,于是当那只大手伸向自己的时候,杨欣尖叫一声跳了起來,握着那柄蓝莹莹的匕首,冲新郎吼道:“你不许你碰我。”
新郎杨昊登时就愣在那儿了,契丹的女子果然豪迈,洞房之夜也操刀弄剑的,不过看着小娇妻稚嫩的面庞,惶恐的神色,他立即收敛了要开玩笑的心,比划着跟她说:“如果你不喜欢,我绝不碰你。”为了表白自己的真心,杨昊真的就抽出一条毛毯和一条被褥向门外走去,
这可让杨欣傻了眼,哪有新婚之夜新娘把新郎赶出去的道理,这种极其无礼的行为足以让整个家族蒙羞的,她紧张地看着这一切,在判断出杨昊确实要离开时,她仍不住一跃而入,赤着脚跳下床从身后抱住了新郎的腰,杨昊笑了,他把已经卷好的毛毯被单丢在了床上,就捉住了她的手,当杨欣不得不近距离面对他时,一张脸羞的红到的耳根,她略显慌乱地解开了自己的衣带,把那一对尚未丰满的蓓蕾展露在这个陌生男人面前,
杨昊按住了她的手,阻止了她下一步的动作,然后柔声地安慰她:“那个,我累了,要不明天,好吗。”
杨欣被针扎似的缩回了手,神情变的落寞起來,这让杨昊不安起來,他想起了临近的乙室部流传的一个传说,那是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勇敢的猎手,他抢娶了临近部落的一位姑娘,初夜交欢时,新娘因为护疼,哀求他离开自己,英雄恼了,拔出刀子就剖开了新娘的肚腹,割了她的肝,烤熟当下酒菜,
这还不能消去他的愤怒,他把新娘的人皮完整地剥了下來,晾干了,在里面塞上干草送还给了岳父,他的大妻舅來为妹妹报仇,被他一箭射杀,小妻舅也來报仇被他射伤了腿,夺了他的弓箭,剥光他的衣裳,将他绑在野外的一根木桩上,
第二天,人们发现可怜的人已经被蚊虫吸干了血,肤色青紫,面如骷髅,
人们敬仰这位英雄的壮举,以致大可汗最后不得不宽恕他的罪过,留他在帐中效力,他带兵收服了奚人和室韦,又打的回鹘丢盔弃甲,连遥远的大唐也知道了他的姓名,边镇的城门每日过午即关闭,直到英雄之花在草原上凋零,
人们一代又一代地传颂着他的故事,毫不避讳他杀妻的过错,草原人就是这么一种心态:强者,强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弱者即使浑身贴满道德的标签也是别人耻笑的对象,
想通了这一节后,杨昊心中的罪恶感消失的无影无踪,他异常温柔地弄着羞颜未开的妻子,点燃她重为人的生命之火,那晚以后,她变得异常依恋他,无条件地相信他,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含着绵绵的爱意,杨昊心里充满了愧疚和不安,娶她并不是因为爱,也无欣赏仰慕的心思,这完全是一桩**裸的交易,
现在这个天真纯洁的女子就这么无保留地爱上了自己,又让自己如何自处,杨昊只能小心地加倍地疼爱她,变着法儿去讨好她,希望这个被爱意重婚头脑的小女人不要那么早窥破自己内心的龌龊、冷酷,
又是一个彻夜难眠的夜晚,在窗外泛白的时候,杨昊用双臂当做枕发了一阵呆,杨欣赤 裸着身体在屋里走來走去,那两个未长成的**雪白挺翘,应着细碎的步子一颠一颤的,
杨昊喊道:“把鞋穿上,地凉呢。”杨欣回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上翘起來,露出齐整结实的牙和鲜红的牙龈,她用手帕兜着一些牛肉干重新上了床,先在杨昊嘴里放了一根,自己也叼了一块,
“后天是阿舅的寿辰,我想去一趟,你去吗。”杨欣漫不经心地问,见杨昊沒回答,便把头转了过來,她顿时吓的魂飞魄散,仅仅一刹那的时间,杨昊竟圆睁双目,撕咧着嘴,如一条僵死的野狗一样,嗬嗬嗬地喘气,
杨欣吓得魂飞魄散,丢了满手的肉干,拼命推搡着自己的夫君,杨昊浑身剧烈地颤抖起來,他双手抖拼命扣抓自己的喉咙,发出“咯咯咯”的恐怖声响,却就是说不出话來,杨欣急了,她一跃而起跳下床,飞奔向外:“來人呀,來人呀。”
她刚喊了两句,杨昊就在身后哈哈大笑起來,他坐在床上拍着手,笑的眼泪都快下來了,杨欣目瞪口呆,她无法理解这是杨昊跟她开的玩笑,她冲到杨昊身边,疑惑地看着他的脸,问:“你,你好了吗。”待确信杨昊确已安然无恙,她眼圈一红,泪水就簌簌直落,她搂着杨昊的脖子哽咽着说道:“如果你死了,我也跟着你死。”
大清早起來杨昊本想开个玩笑,却换來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感动,他苦笑着,心里暖洋洋的,他搂紧杨欣说道:“你丈夫命大,不会丢下你的。”他心生感慨,自己虽与多个女子有过感情瓜葛,肌肤亲昵,到头來却是怀里的这个胡女更像自己的正牌妻子,
门外传來细碎的脚步声,东方兰压着嗓子问:“大哥,您沒事吧。”
“沒事,你嫂子刚做了个噩梦。”
东方兰觉得有些意外,这是杨昊第一次对外称杨欣为“你嫂子”,当初,他耗费山寨五分之一财产迎娶杨欣,引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为平息众意,他只得坦白自己娶杨欣的考量,山寨中从此知道这个娇小、羞怯,相貌并不出众的胡女只是联系山寨与乌隗部的一枚棋子,对她的尊重也仅限于嘴里的 “夫人”二字,
“夫人”、“嫂子”,不仅是词义上的差异,内涵更有天壤之别,因此在这日迎接吴成龙的宴会上,头领们向杨欣敬酒时的措辞、神态就有了很大不同,杨欣到底还年轻,她还不能从这细微的差别中体味出更深一层的含义,
吴成龙一直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杨昊向他敬酒时,他的眼神里就闪烁着一丝异色,该说的他一定会说透,不想说的,猜也是白猜,
宴席散后,吴成龙坐在了杨昊的书房,杨欣捧來了醒酒的酸草汤,吴成龙忙起身迎接,杨欣矜持地笑着,说:“吴大人是贵客,该让我來伺候你。”
杨昊听她话说的暧昧不清,就对她说:“我跟吴大人有话说,你先下去吧。”杨欣拿瞪了杨昊一下,才捧着托盘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这一回眼眉已经弯成了两道月牙,
吴成龙低头品茶,久不发言,杨昊也捧着茶喝,并不急着催促他,这中间來杨欣的侍女杨美、杨目來了两次,一个送干果,一个送梅汤,杨欣出嫁时带了二十名女仆,留了六个在身边服侍,其余的都粗使在外,半年中多半配了人,
四人都以杨为姓,以“美目盼兮,巧笑倩兮”两句为根据,取名杨美、杨目、杨盼、杨巧、杨笑、杨倩,六个人改了汉名,穿上汉装,乍一看与汉家女子无甚区别,
到六人中最乖巧的杨巧來续茶时,杨昊对她说:“回去告诉夫人,这边不用侍候了。”杨巧却站着沒走,磕磕巴巴地问道:“夫人挑了杨美、杨笑给吴大人侍寝,大当家帮问问吴大人愿意吗。”吴成龙闻听这话忍俊不禁,将嘴里的一口茶喷了出來,杨巧忙从袖中拿出手绢给吴成龙擦拭,
吴成龙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对杨昊说道:“尊夫人好意,在下心领,我独身惯了,不必有人侍寝。”杨昊笑对杨巧道:“你去告诉夫人,我与吴大人要秉烛夜谈,不必费心找人侍寝了,再跟杨目说一声,让她准备几样小菜送來,醒了酒就觉得肚饿。”
杨巧唉了一声退了出去,吴成龙笑问杨昊:“这几个姑娘倒是有趣,看來你虽做了契丹人的女婿,心却还向着大唐。”
杨昊哼了一声,缓缓说道:“生于斯长于斯,是大唐不容我,非我弃大唐。”
吴成龙就问:“若有报效朝廷的机会,你愿捐弃前嫌,重新为国朝效力吗。”
杨昊默然一叹,仰面靠在椅背上,呆坐良久才道:“此间无外人,有话请直说。”
吴成龙沒有再兜圈子,他从束身衣袋中取出一份用白绢书写的密信,放在了桌子上,白绢的一角绣着刺马营独特的盾牌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