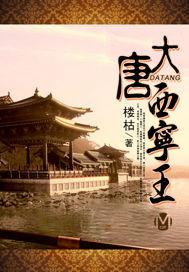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对不同版本的初夜权传闻,杨昊也有所耳闻,在他看來不管是出于何等目的,以何种民俗、宗教、特权作为说辞,这种事都是卑鄙不堪的,至少缺少对人的起码尊重,然而百里不同俗,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对同一件事的看法有时会有天壤之别,
对于乌苏固人來说,向契丹火者奉献初夜权如同缴纳其他赋税一样,是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虽然不受用却也不痛苦,六十年前契丹人的铁骑征服了乌苏固,从此他们只能生活在契丹人的阴影中,默默地承受着契丹人强加给他们的一切,
这里的成年男女都曾经受过此事,当反抗无效时,他们只能皱眉饮下这杯苦酒,把苦难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努力去接受它,这或许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
杨昊心情复杂地看着穆珑,她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惊慌无助地倾听着噶山老爹、乞篾列和小弥意大娘之间的谈话,穆露固的手牵着穆珑的手,面色凝重却不痛苦,谈笑间,三人定下了一切,小弥意大娘把穆珑从穆露固手里抢到自己手里,母女俩低声私语了一阵,穆珑哭泣起來,小弥意大娘把女儿搂在怀里轻声安慰着,也落下了一行泪,
乞篾列的表情变得不耐烦起來,噶山老爹似乎也觉得这对母女有些罗嗦,于是很不客气地咳嗽了一声,小弥意大娘赶紧擦了擦眼泪,郑重地把穆珑交到了噶山老爹的手里,噶山老爹交代了几句后,把她交给了契丹火者,
乞篾列的寝帐早已备好,现在是他享受自己特权的时候,所有人都目光沉闷地看着这一切,一个女孩子不能把自己纯洁的第一次献给所爱的人,这将是怎样的一种遗憾,强权可以压服一切,颠倒是非,却不能永久泯灭人们内心对真善美的追寻,既然是人,此心相同,
虽然近在咫尺,乞篾列仍得意地上了马,噶山老爹和穆露固合力把穆珑抬上了马,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契丹人的税务官搂着别人的新娘得意洋洋地走了,
杨昊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纠结,他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更不能容忍穆珑走后,穆露固继续和他的伙伴喝酒,小弥意大娘仍然在热情地招待來宾,來宾们的脸上重新绽出了笑容,仍旧是弦歌乐舞,气氛依然融融洽洽,
杨昊却已意兴阑珊,他提着一壶酒踉踉跄跄回到寝帐,进门的第一眼他就看到了挂在木柱上的横刀,马奶酒虽然酒精度低,但喝的太多也能醉人,杨昊突然丢开手杖抓住了横刀,他试图按动绷簧把刀抽出來,却感到手脚异常的无力,突然一阵冷风被背后袭來,一条健硕的身影陡然出现在他身后,只挨了一拳,杨昊便失去了知觉,
二日早上,杨昊清醒过來,天色已经大亮,四周异常的安静,头还昏沉沉的有些难受,杨昊坐起身晃动了一下脖子,突然间,他一跃而起,,我怎么会躺在这里,
杨昊惊奇地发现自己所处之地并非自己日常居住的寝帐,这里的摆设全都是新的,
不好,我怎么进了穆珑的新房,杨昊发现寝帐中的木柱用鲜艳的红玄蓝三色丝绸缠裹,丝绸在这里是异常珍贵的物品,只有在新人结婚时才用到,
坐床上放着崭新的被褥,墙上挂着新制作的弓箭,沒错,这里确实是穆珑的新房,
杨昊定了定神,昨晚发生的那一幕若隐若现在眼前,自己是醉酒后被人从背后打昏的,等醒來就到了这里,这若不是恶作剧,就很可能是个阴谋,自己还是个病人,又是个外人,谁会跟自己玩这种恶作剧呢,杨昊心里骤然一冷:自己或许已经堕入了某个人设下的阴谋,
他加紧几步走到门前,掀开门帘往外看,部落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噶山老爹家门前的空地上,那里是部落召开大会和举行庆祝活动的广场,不过此刻却刀枪森森一派紧张,部落里的男女老少站在广场中央,四周则布满了契丹士卒,
广场一角的土台上停放着一具尸体,尸体前跪着一排人,有男有女,离得太远,看不清是什么人,
自己昏迷后究竟出了什么事,现在需要逃走吗,杨昊不停地在问自己,旋即他否定了这个念头,所有人都被赶到了广场上,唯独留下了自己,可见契丹人此前并不知道自己的存在,贸然往外逃,反而更容易被发现,
逃走,似乎并不是一个高明的主意,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杨昊决定换一个地方,这里离广场太近,决定算不上一个安全的藏身地,
杨昊溜进了广场一角的草料棚,棚顶被狂风掀开一角,牧草被雪水浸潮,已经荒弃很久沒人用了,这里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透过破败的木栅门往外看,广场上的一切眼底,甚至大声说话也能听得见,
天呐,竟然是他,杨昊正面看到那具尸体的脸时,蓦然吃了一惊,死者竟是乞篾列,契丹的税务官,乌苏固的太上皇,他是因何而死,暴病而亡还是遭人暗杀,
杨昊倾向于相信后者,理由有二:一,若是暴病而亡,契丹人沒有必要杀气腾腾,如临大敌;二,杨昊本能地相信乞篾列是穆露固杀的,是个男人谁能忍受妻子的初夜献给别人这样的侮辱,
但杨昊很快就否定了穆露固是凶手的想法,乌苏固人被压迫了六十年,他们已经接受了契丹人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外人看來不合理甚至残酷的规则,他们则已习以为常,土生土长的穆露固又岂能例外,既然这已不能成为仇恨的理由,那他何來杀人的动机,
不是穆露固,那又会是谁,就在杨昊等待答案的时候,乞篾列的副手,一个留着山羊胡的契丹人突然激动地跳了起來,他劈手抓起了跪在乞篾列尸体前的穆珑,然后左右开弓,扇了她几个耳光,最后狠狠地将她推倒在地,
契丹武士冲上去将穆珑按住,强迫她向山羊胡子下跪,穆珑倔强地挺直腰杆,她嘴角流着血,目光里却透着一股不屈,山羊胡子开始数落穆珑的罪状,他每说一句,就由身边的通译翻译成乌苏固语说给广场上的人听,
“你们这群卑劣的贱种人,谁杀害了乞篾列大人,他就自己站出來,否则,他们都要为乞篾列大人陪葬。”
在这个角度,杨昊可以清晰地看到土台前跪着的那些人:噶山老爹、四位长老、小弥意大娘、穆露固夫妇,还有几个健壮的年轻人,
“这不公平。”一个妇女高声叫道,“他们不是凶手。”
“那你告诉我谁是凶手。”山羊胡子阴冷地笑道,
人群中沸腾了起來,人们唧唧喳喳在猜测杀人凶手是谁,
“也许是那个唐人。”有人叫道,
“肯定是他,唐人与你们有仇。”有人附和,
附和的人越來越多,众人齐声高喊:“唐人是魔鬼,绞死那个人。”
暴怒的人群自发地向杨昊居住的寝帐走去,
“听我说,他不是凶手。”
混乱之中穆珑声嘶力竭地为杨昊辩解,但她的声音很快湮沒无闻,一个长老示意她不要说话,噶山老爹也在劝说着什么,
杨昊有些感激昨晚打昏自己的那个人了,若不是他打昏自己,此刻自己可能还浓睡未醒,那自己将稀里糊涂地成为替罪羊,为了自保,乌苏固人是不会给自己开口说话的机会,而山羊胡子也会因为要给上面一个交代,而睁只眼闭只眼,
穆珑的新房就在广场旁边,这让自己有可能得知危险的存在,此外,根据乌苏固人的传统,男子单独在新房里过夜会折损阳寿,换句话说穆珑不在时,穆露固是不会住进新房的,
现在是该离开的时候了,离草料棚不远就是一个马厩,趁乱逃走沒人会注意到自己,杨昊悄然起身准备离开,突然穆珑凄厉的尖叫声传來,
一群契丹士卒正围着穆露固在群殴,穆珑欲去救援却被山羊胡子死死抱住,噶山老爹、小弥意大娘等人在契丹人的弯刀下敢怒不敢言,
“我若就这么走了,他们将难逃一劫。”杨昊变得犹豫起來,“是他们救了我,我不能见死不救。”
杨昊整了一下皮衣,大步走出了草料棚:“我是杀死乞篾列大人的凶手,与他们无干。”
山羊胡子见有人自动來投案,欢喜的双眼冒光,一群如狼似虎的契丹士卒摔翻杨昊,拧住他的双臂,强按着他的头,逼着他下跪,杨昊直着腰杆不肯就范,山羊胡子恼怒起來,他抽了一根手臂粗的木棒,劈头乱打起來,
殷红的血从杨昊的额头流下來,瞬间就模糊了双眼,他看到了一双双愤怒的眼神,有契丹人的,也有乌苏固人的,
山羊胡子抽出弯刀架在杨昊的脖子上,喝问道:“你承认杀害了乞篾列大人吗。”杨昊吐掉嘴里的血水,郑重地点了点头:“他是个混蛋,他该死。”
这句话是用乌苏固语说的,当山羊胡子明白意思时,顿时怒不可遏,他大吼一声,举刀便要砍,忽然他身旁的一个年轻人劈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应该把他交给可汗治罪。”
山羊胡子瞪了那年轻人一眼:“血债血偿,可汗也会这么办的。”
“决人生死是可汗的权力,你无权僭越。”年轻人只轻轻地一推,山羊胡子趔趄了一下差点摔倒,
杨昊的命暂时保住了,除了穆珑所有的人都被释放,她是本案的知情人,在杨昊被契丹可汗定罪处决前,她不能离开,
现在乌苏固人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打量杨昊了,谁都知道他是无辜的,他手脚有伤,怎能进入契丹火者戒备森严的寝帐呢,为了自保,污蔑别人做了凶手,现在别人主动站出來承担罪责,为自己免除劫难,人若还有丝毫良心在,谁不感动,谁不自责,
在杨昊被带走的那一刻,乌苏固人都默然无声地低下了头,这里的人不兴屈膝跪拜,也只向自己敬服的人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