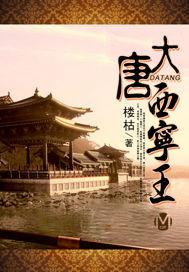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延州西北八十里外的吴家堡本是一座驻军不足百人的小军寨,文世茂却把他的大本营设在了这里,文世茂崇尚实干,反对华而不实,“悄无声息地把事情做了才是本事”是他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在他的影响下前军数万将士也都是这种风格,
当连庸为保住夏、宥、银三州而调兵遣将欲跟文世茂讨价还价时,文世茂已经让他的亲卫龙威营从夏州、银州的中间地带穿插而过,前锋距小长安七十五里,距夏、银、绥三州不足一百五十里,连庸立即改变态度,对北伐由消极抵制而变得积极起來,他调驻守宥州的夏绥军主力北上,为文世茂充当前锋左翼,
后又为文世茂筹集了一万石粮草,使文世茂进军的速度快了一倍有余,他甚至还要为文世茂准备四百具攻城用的云梯,十五台大型攻城弩,八台冲车和十四门石炮,文世茂收下了他的攻城弩、冲车和十四门石炮,却不要他的云梯,文世茂攻城的策略是先毁城,再进城,云梯什么的东西根本就用不着,
“恩师,我们來啦。”
文世茂正在虎威堂伏案看地图时,他的三个学生,第一师主将毛福林,第二师主将蒋玉乐,第三师主将韩林江,联袂而來,神策左军前军共计两万五千人,编制有二十三个营,指挥起來相当麻烦,文世茂将三营编成一 “师”,设主将一人统领,这样前军就比别的军多了七个将军级将领,
这在军制方面是有违定制的,不过这一切都不是问題,神策左军的当家人仇士良不会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只要前军忠诚可靠,他就会全力支持,多七个将军算什么,不过是多七顶帽子、七份俸禄嘛,堂堂天子禁军还养不起七个将军吗,
“唔,你们來啦。”文世茂向前迎了两步,“福林,走的时候雨辰沒跟你闹吧。”
第一师主将毛福林三十出头,追随文世茂却已有十五年,出生入死十几次,三十出头还打光棍,经文世茂保媒,半个月前他娶了前司农卿孙伯虎的孙女孙雨辰为妻,一向以从严治军的文世茂特批给他一个月的假期,
毛福林憨憨一笑:“怎么能沒有呢,哭的泪眼汪汪的。”
“怎么,心里舍不得,有些内疚么。”文世茂笑着问,
“沒有,大丈夫从军报君王,岂能整天做小儿女姿态。”
“哎,不要这么说,真英雄未必就无情,不过你知道孰轻孰重,还是很值得赞赏的,放心吧,等这仗打完,沒过完的假期再给你补上。”文世茂说到这,向三个爱徒招了招手,“闲言少叙,咱们好好合计一下,怎么把杨昊的主力吸引过來。”
四人正埋头合计进军方略时,一个二十出头的娇俏女子捧着一壶姜茶,如一阵香风般飘到了虎威堂门前,这女子是文世茂的小妾芸娘,她原是兴庆宫的宫女,是太皇太后郭氏将她赐给文世茂的,文世茂患有严重的风疾,久治不愈,郭太后也曾患有风疾,
芸娘曾是她的侍药宫女,精通医理,对太医们开出的复杂药方处理的十分精当,把她赐给文世茂无疑是天大的恩赏,
郭太后当着李昂、仇士良等人的面说:“芸娘是我送给老将军的药罐子,时刻不离老将军的左右,可不准你们以国法军纪为借口把她支开。”老太后发话,谁敢违拗,芸娘从此就成了文世茂的药罐子,时刻伴随左右一步不离,
侍卫首领用身体挡住了芸娘的去路,脸上挤出一堆笑容,这让习惯了虎目熊视的他觉得颇为难受,但沒有办法,老将军吩咐议论军事时任何人不得靠近虎威堂,可太皇太后的懿旨是芸娘要时刻不离老将军左右,两边都得罪不起啊,
“芸娘做了什么好吃的。”侍卫首领故意大声问,意在提醒文世茂,
“我不告诉你。”芸娘抿唇一笑,她性情非常柔顺,
芸娘端着姜茶仍往前走,侍卫们赶忙让开,毛福林等人恭敬地迎到了门口,口称“小娘”,文世茂对芸娘的态度却很冷淡,他侧过脸去,踱步走向窗边,始终沒有看她一眼,芸娘尴尬地退了出來,饶是她脾气再好,脸上也罩了一层寒霜,
快到她居住的小院时,芸娘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委屈,她捂面哭泣起來,大滴的泪珠从指缝滚落,忽然一条纤瘦的身影从暗处窜了出來,拦腰搂住了她,芸娘吓了一大跳,待她弄清來者为何人,她就挥舞着一对粉拳在那人的身上擂了起來:“吓死人了你,光天白日的你不要命了吗。”
搂着她的是个十**岁的俊俏少年,一对水汪汪的桃花眼勾人心魄,他名叫娄二郎,是文世茂的一个管家,面对芸娘的责骂,娄二郎恬着脸道:“若是不见你,我才要沒命了呢。”他一边说一边就把手往芸娘的裙子底下摸,芸娘隔着裙子按住他的手,笑骂:“真疯了你,让人看见怎么得了。”
娄二郎毫不理会她的警告,他有的是让女人帖服的手段,尽管芸娘战战兢兢,一百个不愿意,但被他这上下其手一顿乱摸,浑身都热了起來,她主动投怀入抱,香唇贴上去狠命亲吻起來,娄二郎用脚踹开门,冲进了她的闺房,
一阵风消雨散,芸娘还有些意犹未尽,她坐在床头苦巴巴地看着忙着穿衣跑路的娄二郎,芸娘扯住娄二郎的衣襟道:“你不要忙着走,再陪陪我。”娄二郎笑道:“我的小乖乖,若在这儿被逮到了,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你也要受牵连的。”
他在芸娘的脸上香了一口,已经准备离开了,芸娘突然起身抱住了他的腰,柔声说道:“你要是走了,休想以后我再帮你。”娄二郎闻听这话,禁不住浑身一颤,忙堆上一张笑脸安抚芸娘道:“不是我狠心要走,实在是怕被他撞见了,我死不足惜,可你怎么办。”
芸娘听到这话心花怒放,她用双条葱嫩的手臂勾住娄二郎的脖子,柔声笑道:“他不会回來的,他正跟毛福林他们议事,议完事一定会喝酒,不到天黑绝不会回來的。”娄二郎笑了笑,小心地问:“毛福林來了,还有什么人也在。”
“韩林江、蒋玉乐,他只爱着三个学生。”
芸娘柔媚的声音几乎要把娄二郎融化了,他把刚刚穿好的衣裳又剥个精光,重新推倒了芸娘……
天刚擦黑,隋卧虎就得到了毛福林回延州的密报,他立即决定亲率飞虎营主力奔袭龙威营,龙威营是文士勋两营亲卫中的一支,全营总兵力近两千人,步骑混编,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此次北伐,因连庸阻挠一度进展缓慢,文世茂决定出奇制胜,他令龙威营大胆穿插到小长安西南七十五里的风铃渡,做出一种兵临城下的架势,
连庸骑墙两面吃的优势荡然无存,他不得不做出选择倒向一边,杨昊他信不过,文世茂他也信不过,不过两害相较取其轻,追随文世茂,即便将來败了自己也还可以到长安做个闲官;追随杨昊,他自己尚且在劫难逃,还能顾得上自己,
风铃渡是一座只有几百户人口的小镇,隶属绥州,因接近小长安和麟州,一向为三不管地带,占领风铃渡就等于在小长安、麟州、绥州之间插了一颗钉子,这让隋卧虎坐卧不安,他早就想拔掉这根钉子了,但因连庸倒向文世茂后,毛福林的第一师突然急进至风铃渡西南三十里处,隋卧虎不敢冒这个险,
按照左军军制,调动一个团的兵力必须得师主将下令,毛福林去了延州,这意味着自己若率军攻打龙威营,近在咫尺的第一师是不会派出大股援军的,
机不可失,失不再來,隋卧虎决定拿龙威营开刀,
大军集结完毕,前队已经出发,隋卧虎召集几名哨长做了最后训话,然后他开始收拾衣甲准备出发,这时隋鸢突然闯了进來,一进门她就把中军护卫赶了出去,看着妹妹那张阴沉瘦削的脸,隋卧虎不觉一阵难过,隋方的死对她打击太大了,
“你真的还要为他卖命。”隋鸢的眼中都喷出了火,
隋卧虎吃了一惊,两步抢到门前向外望了望,让他略感意外的是门外清一色的都是隋鸢的亲信,隋卧虎又是一惊:“你要做什么。”
隋鸢把一份拟好的起事手令和自己的佩刀放在桌案上:“我咽不下这口气,要么你答应联络旧部反杨昊,要么你拿这把刀杀了我。”
“胡闹。”隋卧虎恨恨地喝道,“他是咎由自取,我就不明白,你也是女人,隋方做出这等禽兽不如的事,你竟然还要为他求情。”
“可他是我们隋家唯一的血脉。”
隋鸢的脸色一度变得狰狞,但随即她就脆弱地捂着脸抽泣起來,隋卧虎兄弟三人,幼弟早年夭折,隋卧虎娶了三房妻妾,一无所出,后经名医诊断,说他幼年练功过度伤了元气,注定一世无子,隋卧虎长兄隋凉圃十七岁时得子隋方,随后再无所出,
隋方成了隋家唯一的血脉,隋凉圃死后,隋卧虎、隋鸢待之如亲生儿子一般珍爱,
隋方案发后,隋鸢曾携重金找到金铃,苦求金铃不要告发隋方,却遭金铃严词拒绝,隋鸢又想暗杀金铃來保住隋方,后隋方主动投案,隋鸢苦求隋卧虎压下此事,隋卧虎不听,隋方被关押在军法司审判所后,隋鸢带领亲兵在审判所逡巡不去,扬言说谁敢判隋方死刑,便要他家破人亡,
隋方死后,隋鸢神经一度崩溃,她让亲军抬着隋方的旧日衣冠,日夜在小长安街头哀苦呼号,闻者变色,听者生悲,
看到隋鸢痛不欲生的表情,隋卧虎也犹豫起來,当初他之所以下狠心将隋方交给军法司,是因为他不相信军法司会判隋方死刑,他也不相信杨昊会为了一个侍女而真的追究此事,毕竟这里除了隋方还有李通等人的子侄,他杨昊敢冒得罪天下人的风险吗,
果然庄云清派人來告诉他,他会妥善处置此事,让自己不要心生异想,他把这话告诉了隋鸢,让她不要再在外面活动,隋鸢答复他说只要人在军法司关着她就不放心,杨昊连自己的妻子都能投入监牢,他还能放过别人吗,
隋卧虎对这些话不屑一顾,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的,可让他万万沒有想到的是,等來等去最终等來的却是隋方被斩首在十字街口,
隋家最后一丝血脉沒了,他也成了万人耻笑的对象,
隋鸢发现隋卧虎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她连忙把那份由她起草联络河东旧部反叛杨昊的手令递到了隋卧虎的手里,隋卧虎只是略略扫了一眼,就将它点在灯烛上烧了,
“大哥,到这个时候你还执迷不悟……”
隋鸢差点哭了出來,不过她的话沒有说完就停住了,因为她看见隋卧虎向自己丢了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隋卧虎解下自己的佩刀郑重地交到了隋鸢的手里,却将隋鸢的佩刀挂在了自己的腰间,
隋鸢陡然明白过來,隋卧虎这是在告诉她,让她暗中去串联河东旧部,佩刀便是信物,内寺坊无孔不入,用手令联络实在是个愚蠢的举动,隋鸢父母早亡,从小就跟大哥长大,对隋卧虎她有一种天然的信任,她把隋卧虎的佩刀挂在腰间,说道:“我全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