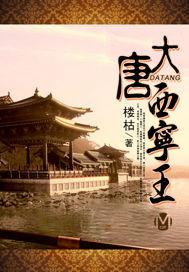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晴儿这两天一直忙着筹办伍章和朱兰的婚事,自从伍章在军械司新工厂的池塘里救下了朱兰,两个人就结成了一对欢喜冤家,闹來闹去,终于在一个月圆之夜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半个月后朱兰谎称自己怀孕,要伍章娶她过门,伍章慌了手脚,竟躲着不敢见人,朱兰心痛欲碎,这一次她沒选择投湖,而是坚定地堵在门口等伍章出來,
晴儿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她把朱兰叫到面前问明了情况,就让人把伍章带了过來,她当面问伍章:“朱兰说你奸骗了她,是真是假。”伍章情知事情已经暴露,忙叩头认罪,晴儿拍案喝道:“來人,把这个畜生拖去交军法司论罪。”
伍章垂头丧气,一语不发,屏风后的朱兰沉不住气了,她冲出來“扑通”一声跪在晴儿面前,矢口否认是伍章诱骗了她,献身是她自己心甘情愿的,她流着泪恳求晴儿不要惩处伍章,晴儿故意板起脸说:“你不要怕他,凡事有我给你做主。”又喝问侍从:“愣着做什么,还不拖走。”两边侍从押着伍章要走,
朱兰急了眼,拖着伍章的手臂不肯放:“夫人要杀伍章,请将朱兰也一起杀了吧,我们在人间不能成夫妻,就到阴间做鬼夫妻吧。”伍章听了这话甚是感动,含着泪道:“是我辜负了你,夫人杀我我无怨言,你好好活着忘了我吧。”朱兰劈手扇了伍章一巴掌,怒斥道:“懦弱之言,死有什么好怕的,人沒了所爱,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伍章羞惭地低下了头,只剩哭的份了,金铃看的眼圈红红的,忙來劝伍章和朱兰:“你们两个若是心里都挂念着对方,何不请夫人做主结为夫妻,夫人是个菩萨心肠,你们真心求求她,她一定会成全你们的。”
二人这才缓过神來,忙跪求晴儿为自己主婚,
晴儿见目的已经达到,心中一喜,却又故作为难道:“我可以为你们主婚,不过丑话说道前头,日后你们闹不和可不许埋怨我。”二人喜极而泣,忙叩头称谢,
伍章父母双亡,相依为伴的只有一个瞎了眼的姑姑,朱兰有舅父,但因表哥的那一桩事,也不想再见面,晴儿便做主在丰安为他俩操办了婚礼,婚礼一切准备停当后,杨昊才得知消息,一时又惊又恨,把伍章逮到骂了一顿,责他不该瞒着自己,
又讥笑晴儿道:“你再这么下去,就要成丰安头号媒婆了,我问你,这两年你撮合成了几对。”晴儿扳着手指算了一遍,人太多,已经算不清了,叹了一口气笑道:“成人之美,乃积德之善事,多做几件又何妨,这也是为你消灾祈福啊。”
杨昊笑道:“是是是,天下贤能无过于吾妻,听说你最近在忙着筹办一场水路道场,是真的么。”晴儿笑道:“是真是假,你真不知道么,朔方一战死了那么多人,不为他们超度怎么行呢,你届时也去一趟,不管心诚与否,也在佛祖面前混个脸熟嘛。”
杨昊道:“实话跟你说,上面大总管信道恨佛,你说我还能去佛爷那儿露这个脸吗。”晴儿吃了一惊,忙道:“那,我也不去了,咱们该信道家吧。”杨昊想了想道:“那就不必了,多拜一家何错之有呢,毕竟当今天子也信佛嘛。”
晴儿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了什么:“我记得永丰城西有座德清宫,据说原先很繁盛,这两年破败了不少,要不舍他一座殿宇,也显得咱们心诚嘛。”杨昊嘻嘻一笑,在晴儿粉嫩的脸蛋上捏了一把,赞道:“到底还是夫人想的周道,悄悄地去干,不要闹的鸡飞狗跳。”
晴儿忙推开杨昊的手,脸腾地就红了,娇嗔道:“你好不尊重人。”
杨昊故意大声说道:“我在自己家里调戏老妻管别人何事啊。”晴儿听了心慌,忙來扯杨昊的手臂,杨昊哈哈大笑,忽见庭院中剪花枝的金铃抿嘴在笑,便问她:“你笑什么,我碍着你了吗。”金铃笑道:“若说沒碍着,那是我睁眼说瞎话,可是老爷您一向我行我素,碍着我了,咱又能说什么呢。”
杨昊对晴儿说道:“你看这丫头好不伶牙俐齿,她今年多大了,是不是要给她配个人了。”不想这一戏谑之言,却让金铃陡然变了脸色,泪珠在眼眶中直打转,晴儿急了,忙扯了杨昊一把,问道:“我看你今天好闲,怎么就一点公事也沒有吗。”
杨昊见她正向自己使眼色,又见金铃双肩微微颤抖似乎在抽泣,明白这里定有缘故,于是托词说道:“我确实还有事,你们忙,我先走了。”
晴儿安抚金铃道:“别难过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高兴嘴上就沒个把门的。”金铃抽泣道:“老爷爱戏谑,我自然知道,怎会怨恨他呢,是我太沒计较,怎能在老爷面前使性子呢,我去给老爷陪个不是吧。”晴儿挽住她的手,说道:“我知道你放心不下他,那就去小长安看看他吧,我这边让朱兰來帮衬几天好了。”
一行清泪从金铃的脸颊上滚落下來,她跪拜道:“夫人大恩大德,金铃沒齿难忘。”晴儿扶住她道:“这是干什么,只是出去两天,难道就不回來了吗。”话说到这,晴儿冷不丁地打了个寒颤,一种不祥的预感充斥在心头,
小长安到丰安最难走的一段路叫胡柳沟,方圆百十里都是戈壁沙漠,因为运送给养困难,从南到北八十余里只设了一座驿馆,驿馆分成两部分,后面是公驿,用以招待过往的邮传信使,前面称作私驿,是对外营业的旅舍,
虽然是晴儿身边的大红人,金铃却沒有任何官职,在胡柳沟驿馆,她只能住在私驿,物以稀为贵,私驿的条件十分一般,但房价却高的咂舌,
金铃沒有多少钱,但她却不是一个肯委屈自己的人,她拿出自己一半的盘缠,要了一间上房,为行路方便,她身上穿的是男装,虽然眼尖的跑堂一眼就看破了她的身份,但沒有闲心去点破她,开门做生意嘛,谁跟银子过不去呢,
大热的天,走了一天的路,满身是汗,黏答答的十分难受,因此虽然洗澡水贵的离谱,金铃还是让驿馆往自己房间里送了一桶,泡了个热水澡,洗去了一路的疲乏,太阳一下山,天气就变的凉爽起來,
金铃早早上床睡下,去梦中会她相识三年的情郎了,这是初春的草原,天蓝云白,他们骑在一匹马上,金铃依靠在他的怀里,驰骋在碧草如茵的草原上,白马带着他们來到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流边,两岸的草地上开满了黄色和白色的小花,蝴蝶就在花草间翩翩起舞,他吹响牧笛,用清亮的嗓音唱道:
天蓝蓝的草原,水弯弯的溪流
蝴蝶和虫儿们在花草间歌舞,
白云追着清风,花香追着清流,
他们徜徉、歌唱、沉醉
有两个人儿啊,
并肩坐在天蓝下,依偎在绿草间幸福地歌唱啊,
……
这是金铃刚认识他时听他唱的一曲牧歌,只听了两遍就学会了,可是她还是缠着他教了十來遍,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朦朦胧胧的如同梦境一般,
“有两个人儿啊,并肩坐在天蓝下,依偎在绿草间幸福地歌唱啊,……”
有人在唱歌,是你吗,
金铃一跃而起,却顿时如坠冰窟一般,她被眼前的情形吓坏了,黑暗中,在蚊帐的外面有个人正站在床边冲着自己傻笑,他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健美的身材,白皙英俊的面容,但他却不是他,
“啊,你是什么人,你怎么进來的。”
金铃下意识地蜷缩到了床头,一股呛人的酒气袭來,白脸年轻人似乎醉的很厉害,他目光呆滞只顾着傻笑,金铃定了定神,悄悄地拉开蚊帐往床下溜,因为心慌意乱,下床的时候不小心被蚊帐的挂钩挂住了衣裳,她心里一惊“哎哟”一声惊叫起來,
那年轻人打了个酒嗝伸手來扶她,金铃心慌意乱,手脚并用连踢带打,
醉酒青年招架不住,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忙乱中阴裆又被金铃踢了一脚,他痛苦地蹲在地上呻吟起來,金铃趁机冲到了门外,不想她刚一出门就一头撞进了一人的怀里,那人一个趔趄“扑通”摔倒在地,
他身后的三个醉鬼却拦住了金铃的去路,一个身材高大的浓眉青年醉的不算太狠,看到娇俏妩媚的金铃,顿生淫心,他伸手拦住了意图逃走的金铃,大手摸向她的胸部,
“你住手。”金铃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声音也因恐惧而变了调,
“放手,,撞倒了人还想走。”
浓眉青年粗暴地拉住金铃的手不放,金铃情急之下抱住他的手臂狠狠地咬了一口,不想金铃的反抗却让那青年愈加兴奋,他把金铃推向了自己的同伴,同伴又把她推了回來,四个人就像猫逗老鼠一样,把金铃折腾的昏头昏脑苦不堪言,
末了,浓眉青年一弯身把金铃扛上了肩,大步闯进金铃的房间,把她往床上一扔,解开裤腰带就扑了上去,金铃一边拼死反抗,一边大呼救命,浓眉青年忙來捂她的嘴,却反被她咬住了手掌,疼的冷汗直淋,
这时,先前被金铃踢中阴裆蹲在地上呻吟的青年,扶床站了起來,他对浓眉青年吼道:“废物,滚开。”
金铃的拼死挣扎已让浓眉青年骑虎难下,进不得,退又觉得失了面子,进退两难之际听到这话,忙就坡下驴丢手退了下來,金铃趁机一跃而起,就往外跑,白脸青年拦腰将她抱住,不等金铃动手厮打,便当胸给了她两拳,
金铃闷哼一声,痛苦地蹲了下去,白脸少年扯着她的头发把她扔到床上,扯开她的衣裙压了上去,金铃仍不肯屈服,她还在微弱地抵抗着,白脸少年暴怒起來,结结实实给了她两记重拳,金铃双眼青肿,鼻血长流,
浓眉青年看的胆寒心惊,扯了扯白脸青年道:“三哥,算了……”白脸少年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浓眉青年魂飞魄散再不敢言语,
这时外面三个醉酒青年也赶了进來,见此情形一个个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开口规劝,白脸青年发泄完**,浑身水洗的一般,指着浓眉青年:“老七,你上。”浓眉青年哭丧着脸,哀求道:“三哥,算了。”
“啪。”地一声脆响,浓眉青年脸上重重地挨了一巴掌,白脸青年目露凶光,恶狠狠地指着众人道:“今晚谁要是敢跑,我就弄死谁。”众人一个个垂头低眉,不敢言语,浓眉青年抗不过他,只得哭丧着脸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床,
金铃就躺在那一动不动,再沒有反抗的意思,但双眸中透出的怨毒目光却让人不寒而栗,浓眉青年避开她的目光,趴在她身上草草了事,下床时手脚皆软,走不两步,双膝一软竟瘫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