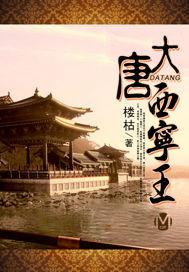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杨昊被关在灵州大牢中整整五天日夜,这中间沒有任何人來讯问过他,他被关在一间防守严密的黑屋子里,既是为了防止他逃跑,也是为了防止有人暗害他,虽然吃喝用度都不算差,但四面冰冷的石墙、潮湿的地面和一股股呛鼻的霉酸味,还是时时刻刻在提醒他:这里是监狱,自己此刻的身份是个囚犯,
有生之年自己再次入狱,上一回是甘露之变时被李训关在大明宫的地牢里,你无法想象金碧辉煌的大明宫里竞暗藏着那么多的地牢监狱,衣紫服蟒的达官显贵们转眼之间可能就会消失在那暗无天日的地牢里,
在这沒有人打搅的五天里,杨昊想了很多事,想的多了,精神不免就有些颓废,他想过永久离开这是非之地,带着晴儿她们隐居山林,晴耕雨读,平平淡淡地过完下半辈子,当然他也知道这只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一切都已经晚了……
自己就像那牢笼里的飞鸟,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扑腾着翅膀,不停地折腾,无非是飞的高一点还是飞的低一点,谁也飞不出这座用金钱、地位、权力和欲望编织成的牢笼,这牢笼无边无际大的能装下世上所有的人,这种想法让杨昊变得更加颓废起來,
五天时间他的胡须疯长了好几寸,发髻蓬松,衣衫凌乱,看起來像是陡然老了五岁,在沉闷的铁门缓缓开启时,杨昊正躺在那张粗陋的木板床上发呆,这让兴冲冲而來的关索吓了一大跳,两个人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拥抱在了一起,彼此的友谊瞬间增进了一大步,铁门重新关闭,关索摸了摸铁门,又敲了敲石壁,确认沒有人在外面偷听时,他终于苦笑了一声,说道:“你这是何苦呢。”
杨昊嘘叹了一声,双手一摊:“这或许能让她好过些吧。”
“今晚她就是别人的新娘了,千恨万错,过了今晚也都该一笔勾销了。”
杨昊低下头望着自己的双手发呆,忽而又“嗤”地笑了一声,像是在自嘲又像是在嘲笑着谁,
“王崇文答应放你出去,条件是永不侵犯朔方,再让出曲泽。”
“都答应他。”
杨昊回答的异常干脆,这让关索产生了一种错觉,杨昊是不是沒听清自己在说什么,这两年丰州对曲泽部可沒少下本钱,就这一句话全打了水漂啦,
“别那样看着我,我听清了,不跟他为难,把曲泽部让给他吗,都可以答应他。”
关索深深地吸溜了一口气,在曲泽部这个问題上自己有一肚子话要说,但杨昊用眼神示意他不要张口,这个问題不是可以讨论的,
“你打算怎么出去,风风光光地走出去,还是偷偷地逃出去。”
“怎么出去都行,只是要越快越好。”
关索默默点头,走到铁门前叩响了门环,囚室里又恢复了黑暗和宁静,但杨昊的内心却是激流暗涌再也平静不下來,李晴大婚在即,这场婚姻对她对自己对王崇文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
筹备多日的大婚庆典终于如期举行,不得不承认朔方人才济济,婚礼操办的异常成功,让上千名來自各地的贵宾赞叹不已,朔方的名望无形间上了一个台阶,
皇家婚礼烦文缛礼自然少不了,否则皇家的威仪和朝廷的体统何在,除了朝廷礼制定例和皇室的各种规矩,灵州本地的婚俗在细节上也多有体现,
即使是博学广识的谢搏之也无法精通所有的礼仪,好在总有人精通这个或那个,谢搏之的高明之处就是能用人所长,又不至于让别人的光芒遮蔽自己、贬折自己,总操盘手的地位和权力是凛然不可侵犯的,
一切的一切都按部就班进行的十分顺利,谢搏之自得的神情越來越浓,喜怒之色溢于言表,他整个人都飘飘欲仙起來,
婚礼进行到最后时刻,一直端坐高堂不露声色的唐氏突然把谢搏之叫到面前,当着龙明月等亲枝贵客的面,罕有地换上了一张笑脸,亲切地说了声:“元参公,你辛苦啦。”“元参”是谢搏之原來的字,因“元”字与唐氏丈夫王璞原名字中的“原”字谐音,谢搏之便将他改成了“庸”字,正是这一字之改,搏之才得到王璞原的信任,因而才有机会三代辅佐王家,成为朔方的元老重臣,
唐氏不仅叫出了他的原名,而且还在名字后面加了“公”字,这对说话刻薄,寡贤少恩的唐氏來说简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谢搏之一面做出受宠若惊的神色,一面却在心里揣度唐氏抛给自己这顶高帽的背后目的,她一定是要自己有所回报,否则那就是太阳从西边出來了哩,
“元参公,剩下还有那些礼仪沒办的。”唐氏是笑着问谢搏之,面相十分和蔼,
谢搏之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是沒有时间去多想了,他如实回答:“不多啦,就是合卺酒,解罗帐圆房啦。”
唐氏点点头,如释重负地说道:“要说天下的规矩还是皇家的最多,似我这样的好太太都快耐不住性子了,若是换了他们年轻人,谁受的了这些。”
围在唐氏身边的一群年轻子侄们听了这话都痴痴地笑,唐氏趁着这个势头跟送亲使龙明月商议道:“时辰也不早了,老身倒是有个提议,能否将这些礼节减一减,免得累着了公主殿下。”“这……”龙明月面露难色,不过很快就表态让了步,“皇家的规矩还是一样不能少,其他的嘛,可以酌情减少一些。”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唐氏脸上绽放成一朵花,她对谢搏之、龙明月、郝赞等一干人说道:“剩下的事就由老身來代劳,各位大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四下里响起一片应和之声,这场婚礼已经整整拖了两个时辰,无人不感到心力交瘁,唐氏的这番话对他们來说实在是个解脱,龙明月、郝赞并无异议,谢搏之有些不放心,唐氏从小就不喜欢王崇文,王崇文执掌朔方后,与唐氏一派势力一直不和,她真能安着什么好心,
安乐州刺史、谢搏之的好友胡坯搂着谢搏之的肩,醉眼朦胧地说道:“哎呀,庸参兄,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您是朔方第一干臣不假,可你能把朔方所有的事都管起來吗,孙子娶媳妇说到底是人家的家务事,你管不了的,该放手就放手吧,走走走,咱们喝酒去。”
胡坯的话倒也提醒了谢搏之,亲不亲一家人,自己再得宠信终究也是个外族,这种家务事自己还是少掺和为妙,想到这他摇了摇头,说道:“不管啦,今天大喜的日子,咱们不醉不归。”
谢搏之等人前脚刚走,一队家丁便关闭了通往外间的所有大门,牙署内堂唐氏的掌控之中,王崇文因为陪酒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此刻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头昏沉沉疼痛欲裂,
唐氏让人取了醒酒汤给他醒酒,王崇文神情稍稍恢复,忽见身边尽是唐氏的人,而不见自己一个亲信,心中震恐不已,但他却不动声色,仍旧装醉不醒,
唐氏鄙夷地看了他一眼,公然斥责:“身为一镇统率,竟也贪杯误事,殿下面前让列祖列宗的脸往哪搁。”叫來两个人架着他往婚房去,
金韬吟与一干花衣卫拦住唐氏一行:“驸马醉成这样,怎么圆房。”唐氏冷笑道:“今日大婚之夜,驸马不进洞房,难道要睡书房吗,罢了,只要殿下舍得去皇家的脸面,老身也任他去了。”
金韬吟一时语塞,又改口道:“不知驸马爷可开过蒙了。”
唐氏闻言却是一愣,不明白这开蒙是何意思,旁边有人提醒道:“姑娘是问驸马爷经历过男女之事沒有。”唐氏愤懑地说道:“我王家子弟家教甚严,岂能与酒色沾边。”金韬吟闻言顿时得了意,冷笑道:“公主乃万金之躯,可经不得生手生脚的轻狂,我劝老太君还是先找人给驸马爷开开蒙吧。”
唐氏冷笑道:“这难道也是皇家规矩么。”
金韬吟笑道:“这是公主殿下定的规矩。”
唐氏嘿然大笑,断喝道:“她是大唐的公主,可说到底也是我王家的媳妇,三从四德也是一样少不了的,自古女子要为丈夫保持完璧之身,何尝听过丈夫要迁就做妻的,说什么公主殿下定的规矩,我看就是你故意刁难我的孙儿。”唐氏一把拉住王崇文就要往里闯,金韬吟大喝一声,众花衣卫“呼啦啦”闯过來将唐氏、王崇文团团围住,
唐氏回身一声喝:“王家子弟何在。”
一群衣着华美的男男女女们此刻却突然将衣襟一掀,亮出刀枪來,他们人数更多,反而将花衣卫包围了起來,这样花衣卫围着唐氏和王崇文,王氏子弟又围住了花衣卫,人人怒目对视,却还是谁也不敢轻易动手,
正僵持之时,李晴的贴身卫士蓝羽突然打开了房门,目光扫过众人说道:“公主有旨,请驸马爷单独觐见,其他人都退下。”
一见事情有解决的可能,王崇文忽然挣脱唐氏的手,向前跨了一步,在众目睽睽之下向洞房走去,花衣卫在退缩,她们的目的只是防守洞房的大门,
“王家的列祖列宗啊……”
正当众人以为一切都将结束时,唐氏突然坐在地上,如同一个泼妇一般,又蹬又踢嚎啕大哭起來,这戏剧性的一幕让一只脚已经跨入洞房大门的王崇文又退了回來,
“祖母,你这是做什么。”
正当王崇文伸手去扶唐氏时,忽然他的身躯一震,继而轰然倒下,四下里一片惊叫声,在他的胸中正插着一支袖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