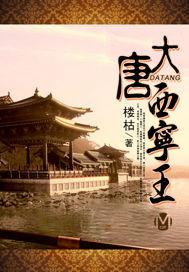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杨昊的请罪疏上呈李炎后不到半个月,李炎的特使又到了丰安,这一次不是萧明月,而是杨昊很久沒见的一个朋友:殷桐香,
甘露之变后殷桐香获罪流放岭南,半途又改放剑南黎州,在那不毛之地待了一年多,殷桐香和先前比有了许多不同,他的脸庞晒成了古铜色,身体变得粗壮,细声慢语也变成了粗声大气,原本明澈的目光多了几分世故圆滑,
两人互诉别后经过,唏嘘良久,杨昊才想起來问他:“几个月前剑南的暴动是不是你们在后面鼓捣的。”
听杨昊说起剑南暴动,殷桐香脸色登时沉了下去,他连连摆手道:“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呐。”杨昊惊诧地问道:“怎么,你们给弄砸么。”
殷桐香闻听这话,一时哭笑不得,四个月前,剑南黎州历书县饥民满地,刺马营趁机策动饥民暴动,打破官府的弹压,攻城夺县,席卷黎州、眉州、雅州、嘉州等四州数十县,饥民抢夺军械粮库,捣毁公署,逮捕官吏,剑南南部地区全部落入刺马营之手,
剑南原本就是刺马营的地盘,仇士良借甘露之变拿到自己手中,四州暴动一起,杨昊就推断是刺马营在背后推波助澜,原本他还在想以刺马营在剑南经营多年打下的根基,恢复剑南应该是易如反掌之事,但殷桐香的这副表情,分明是在说他们败了,
殷桐香抹了一把泪,痛心疾首地说道:“唾手可得的胜利,硬让曾重阳一手给毁了。”
“曾重阳。”杨昊惊叫了一声,“陛下又启用他了。”
曾重阳被杨昊推倒后,一直被软禁在丰州,虽挂着监察御史的头衔,但在丰州只有别人监察他的份,这两年他夹着尾巴做人,不填堵不添乱,不制造一丝一毫的麻烦,去年七月间,曾重阳脚疾发作,遍请名医未能治愈,
曾夫人來到丰安,哀求杨昊放他回长安养病,杨昊一时心软便把人放了回去,此后他一直在家养病,闲來便读书写字,似乎已心灰意冷再无入仕之心,沒想到这一切都是他装出來的,杨昊想到这心里不禁打了个冷战,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了心头,
“你跟他打过交道,也吃过他的亏,想必早已看清此人。”殷桐香惨然笑道,“志大才疏的腐儒,四处插手四处坏事,我实在想不明白陛下为何还要启用他。”
殷桐香狠狠地拍了一掌,悔恨之情溢于言表,做臣子对天子心怀怨怼,这绝对是大忌,殷桐香能在自己面前毫不掩饰这一切,足见他仍把自己当做最可信赖的朋友,
“剑南算是全完了,一万精兵全让曾傻子给断送了,三哥,你知道么,嘉州被围后,我们让百姓出城逃命,曾重阳说危急时刻舍弃百姓,是为不义气,围城三个月后,城中粮草断绝,将士们要突围,曾重阳不肯,说什么将士们走了,留下的百姓定会被屠城,如今只好放下武器求条生路,大伙信了他的话,结果三千弟兄被掠为奴,其他的,背缚双手,像狗一样跪在地上,伸长脖子被他们砍头……”殷桐香捶胸顿足、泪如雨下,
杨昊也不禁泪水潸然,经历了这么多的征讨厮杀,他的心肠早已变的像铁一样硬,但听闻殷桐香的描述心中仍是震惊万端,
“仇士良在剑南究竟有多少兵力,你们拥兵一万,怎么会被围困。”
殷桐香伸出一根手指,森然笑道:“他只有一千人。”
“是左近边镇有人助他吗。”
“一个阉党,谁肯助他,他向南诏国借的兵,围攻嘉州的是最精锐的南诏八镇。”他冷笑了一声,“若不是这个缘由,曾重阳只怕还不会让我们献城投降呢。”
殷桐香知道自己这话若不加解释杨昊是决计听不懂的,于是不待杨昊追问他便解释道:“大和四年,南诏国出倾国之兵洗掠成都,当时曾重阳就在城都,城破后他和数万百姓被掠,南诏国大军将蒙嵯巅驱赶被俘百姓至大渡河边时,跟众百姓说:‘河南就是南诏境,尔等可在此哭别故乡故国,’民众面朝故乡痛哭不止,有数千人跳水自杀,曾重阳也跳了河,可惜他竟沒死,却被吓破了胆,故此一见到南诏人,手也软腿也麻,趴在地上给人叩头投降了。”
殷桐香说的蒙嵯巅是南诏国弄栋节度使,是南诏有名的权臣,他趁剑南节度使杜元颖贪婪昏庸,边境毫无防备之机,倾全国之兵攻陷成都,劫掠财物、人口,南诏国力日隆,蒙嵯巅成为南诏国的大英雄,南诏国也正式取代吐蕃成为大唐西南的最大边患,
杨昊安慰殷桐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人回來了就好,依我看你也不要回长安了,就留在丰州,咱们兄弟一起为国戍边建功。”
殷桐香苦笑着说道:“如今我哪还有心思留在丰安,我这会儿恨不得立即飞去剑南,重整旗鼓,夺回被俘弟兄,为死去的兄弟报仇,既是兄弟,你就该拉我一把。”
杨昊不急不躁地笑道:“那,你要我怎么帮你呢。”
“借我五十万两白银,给我三千套衣甲兵器,最好还有一千匹马,你放心,这些东西我将來会加倍归还给你的。”
杨昊笑着反问:“你手上现在还有多少人。”
殷桐香脸一红:“只三百多一点,不过他们大多都是身经百战的军官,只要有钱有兵甲,立即就能扩充百倍。”
杨昊啧啧嘴道:“就算扩充一百倍,那也就是三万人,南诏是西南大国,二十万大军还是有的吧,以两万对二十万你有胜算吗,再说剑南如今落在了仇士良的手里,你连个屯军筹粮的地都沒有啊。”
殷桐香哑口无言,狠狠地在桌案上砸了一拳,杨昊拍拍他的肩道:“当年大明宫的耻辱,咱们尚且都忍下來了,这点小辱还忍不了吗,你看这样好不好,把你的人带到丰安來,先休整一段时日,再徐图大计。”
殷桐香焦躁地跳起來:“又是徐图大计,我问你,你占着丰州这么好的地方,都两年了为何还是这副不死不活的局面,前日听说你夺了河东,为何又要拱手让出去,在剑南,我们两个月就能拉起一万人马,可你呢,到现在还不到两万吧,似你这般徐图大计,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等不了了,你给句痛快话,给还是不给。”
杨昊哈哈一笑道:“给,你既开了口,我能不给吗。”
殷桐香这才稍稍消了些气,杨昊又道:“不过三千套盔甲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筹齐的,你还是要在丰安待一段时日。”
殷桐香闻言又跳了起來:“我不等,你有多少我带走多少,剩下的你给我送去便是,在你这住久了,我怕堕了心志。”
杨昊点头道:“你不愿留也罢,你且随我到衣甲库去,看上眼的都让你带走。”
西宁军军械司的衣甲库在丰安城西北,占地约五亩,戒备异常森严,知道杨昊要陪朋友來看衣甲,鱼重特意从军械司赶了过來,殷桐香望着那一座座规模宏大的仓库,心中暗自惊叹,这阵势比大明宫的武藏库也毫不逊色,
三人來到最大的一座仓库前,库门上挂着三把钥匙,管库、卫兵和鱼重各持一把,三人同时到场才能开启库门,四名士卒齐心协力才将厚重的库门推开,里面兵甲器械堆放的整整齐齐,足有上万套之多,
殷桐香眉开眼笑,惊呼道:“三哥,有你的呀,这短短两年,你就弄出这副家当來了。”
杨昊哈哈一笑,大方地说道:“尽管挑,合你眼的只管拿走。”
殷桐香道:“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他指着正中的一排:“这些我全带走。”杨昊笑而不言,鱼重提醒道:“殷将军不验一验就带走吗。”
鱼重的笑容有些古怪,似乎在提醒自己什么,殷桐香心里一惊,暗道:“箱子里莫不是空的。”他急忙打开一口箱子,里面确实码放一副明光甲,殷桐香稍稍松了口气,将那副制作精良的明光甲取了出來,明光甲是唐军骑兵制式衣甲,但这件衣甲似乎比普通的要重些,
殷桐香仔细查看了一番,发现胸甲的两片圆护比普通衣甲要大,钢板也更厚实,殷桐香顿时意识到了问題所在,剑南地形崎岖,驻军以步军为主,明光甲是骑兵衣甲并不适合步军穿用,虽说剑南也有骑兵,但南方的马匹一般较矮小,又因道路崎岖,骑兵负重较轻,这明光甲虽制作精良但不合用也等于是废物,
“有适合步军穿用的衣甲吗。”
“有,请将军跟我來。”
鱼重领着殷桐香走到仓库的最里面,这里堆放着大概千余套衣甲,鱼重介绍道:“这边是重甲步军用的衣甲,每件重四十八斤,这边是一般步兵用甲,二十斤左右。”鱼重取出一副轻甲,制作的相当精良,殷桐香看过很是满意,鱼重却忽然说道:“南方阴雨天多湿气大,这种铁甲很容易就会生锈的。”
殷桐香想抽自己一巴掌,这么简单的常识自己竟沒想到,南诏人因为铁少,士卒多用竹甲,既轻便,又耐潮湿,制造竹甲的技术他们视为机密,秘而不宣,剑南唐军多用皮甲,防护力较竹甲稍强,但造价较高,再有就是禁不住水泡,容易发霉变软,
丰州地处北方,气候相对剑南要干燥的多,所用衣甲以铁甲、皮甲为主,这并不奇怪,怪不得杨昊要坚持让自己在丰安住一段时间,原來是这个缘故,自己竟一时竟误会了他的好意,殷桐香的脸红扑扑、热辣辣的,
杨昊道:“你还是留下來住一段时日,让鱼大人给你量身定制一种盔甲,俗话不是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殷桐香沒有再做坚持,随后杨昊又陪着他來到丰州武备学堂参观,武备学堂此刻已经迁到城西,依山靠水,占地有上千亩,学员、教师合计不足五百人,杨昊陪殷桐香來到办学最好的士官系,教室里共有学员二十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士官系培养队级军官,学员多來自军中,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做过伙长以上军官,二、头脑灵活,认识两千个字,虽然人人都知道进了士官系将來前途远大,但这两项限制却将许多胸怀抱负的人拦在了门外,
殷桐香不无挪揄地说道:“能认识两千个字,谁还來当兵,当兵吃粮,讲的是身手灵活、忠勇可靠,你们武备学堂又不是太学、国子监,识那多字做什么。”
杨昊得意地答道:“我这里可是培养将军的地方,自古名将有几个不识字的,你责问我为什么占着丰州这么好的地方,到如今还是这副不死不活的局面,我告诉你,我是再等他们出來,你等着看,三五年后丰州绝对是天翻地覆,十年后……”
杨昊说到这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因为他看到殷桐香正用惊恐的眼神看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