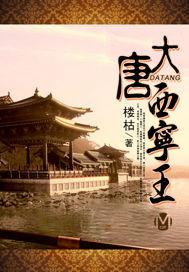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颍王府的东南角有一所偏僻的小院,面朝南三间正房,东面有两间偏房,院中有两株槐花,时值冬日,槐花树上落叶已尽,只剩光秃秃的筋络,这所小院是颍王府太监总管汪春的住所,身为王府总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小院并算不得稀奇,稀奇的是这所小院有两扇门,一扇在王府内,一扇却可直通颍王府之外,
有门可以直接到外面,这表示这是一所独立的宅邸,身为太监能拥有一所独立的宅邸,这是几辈子才能修來的福气,
张莺莺正在清扫地上的积雪,看到汪春吃力地捧回一个紫檀木盒,她丢了扫帚正要上去帮忙,脸上早已笑成一朵花的汪春突然向她丢了个眼神:“快把门关上。”
小院有三间正房和两间堆杂物的偏房,汪春住在正房东厢,张莺莺住西厢,地炉里的炭火正旺,正房里暖烘烘,但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难闻的烟味,
汪春皱了皱眉头:“傻丫头,你怎么不烧白炭呢,白炭沒烟呀。”
张莺莺道:“白炭不好起火,女儿嫌麻烦,故而就用黑炭了……”
汪春呵呵笑了起來,他把紫檀木盒放在桌案上,自己到偏房取來半簸箕白炭,拨开封存炭火的炭灰把木炭一块块架上,汪春一边拨弄着炭火,一边跟张莺莺打趣:“你呀,真是连说个谎也不会,嗯,你是嫌这炭金贵,舍不得是吧。”
张莺莺抿嘴一笑,她默认了,这种白炭是河东进贡來的贡品,耐烧熬火,无烟,无异味,李昂常将此炭赏赐给诸王亲贵,以示宠信,颍王李炎和安王李溶每年可得三千斤,其他王公大臣只能得到一千斤,
颍王府人口众多,若是人人都用,三千斤木炭肯定是不够,若单供李炎王妃用,又肯定有富余,身为大总管,汪春自然有权决定富余的白炭让什么人用,不让什么人用,因此对张莺莺的这种做法颇有些不以为然,
“不管是白炭还是黑炭,都是拿來烧的,王府里有这么多的炭,殿下那边是怎么用也用不完的,我们不用也是给别人用,何苦便宜别人,亏了自己呢。”
张莺莺咬了咬嘴唇,认真地说道:“干爹是王府总管,留点炭自己用,自然是受用的起,但王府里总有些乱嚼舌根的人,他们说的话早晚还是要传到殿下、王妃的耳朵里去的,女儿以为干爹不值得为这点小事在殿下、王妃那边跌了身份。”
“不必管他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殿下、王妃不会因为这个怪罪干爹的。”
汪春故作轻松地说道,其实他心里也清楚,自自己调任颍王府总管以來,下面就一直有一股势力明里暗里在跟自己较劲,李炎几乎从不过问王府内务,王妃体弱多病,无力过问,下面的管事们沒了管束,偷奸耍滑,贪污公帑,把颍王府闹的乌烟瘴气,自己上任后,锐意革新,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因此暗中总有一股力量在跟自己过不去,
张莺莺咬着嘴唇说道:“虽说都是谣言谎话,但说多了听多了也难免成了真话,王妃是一副菩萨心肠,难免给坏人可趁之机,干爹又何苦在这些小事上授人以柄呢。”
汪春听到这心中颇为感慨,沒想到十岁的孩子能有如此见识,又能把话说的这么温婉,颍王妃耳根子是出奇的软,好话歹话她总是一听就信,张莺莺说的不错,自己何苦在这种小事上授人以柄呢,
于是他把剩余的白炭收了起來,提回偏房换了一簸箕黑炭过來,张莺莺见到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心中颇为兴奋,看见桌子上的紫檀木盒,就问:“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
汪春兴致盎然地说道:“你猜猜看,若是猜中了,干爹有赏。”
张莺莺拧眉思索一阵,答道:“多半是金银珠宝。”
汪春不动声色地摇了摇头,道:“再猜一次。”
张莺莺又想了想,道:“若不是金银珠宝,也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对,还是金银珠宝,一定是的,干爹,你说是不是。”
汪春竖起了大拇指:“好见识,你怎知道盒子里装的是金银珠宝。”
张莺莺嘻嘻一笑道:“干爹刚一进门就让女儿把院门关好,可见您并不想让外人看到紫檀木盒,您用了两只手才将木盒放在桌案上,这表明盒子很沉重,这么小的一个盒子里面除了金珠,又会是什么呢。”
汪春把紫檀木盒搬到地炉前,当着张莺莺的面打开盒盖,盒子里是码放的整整齐齐的金条和八颗鸡子大小的珍珠,张莺莺从來沒见过这么多黄金,一时惊得目瞪口呆,汪春拿起一颗珍珠对张莺莺说道:“这一颗珍珠就价值一千两银子,八颗就是八千两,你知道这世上有多少人穷其一生也赚不來这一颗珍珠啊。”
汪春把珍珠放回紫檀木盒,锁好,然后把木盒推到张莺莺面前:“你替干爹好好收着。”
张莺莺惊道:“这莫不是他给您贿赂。”
汪春笑了笑:“先前是贿赂,如今殿下已经知道,那就不算是了。”他微微叹了一声,又说道:“其实这是他送给你的礼物,你好好保管着,将來准有用着它的时候。”
张莺莺对汪春的后半句话有些疑惑不解,这明明是杨昊贿赂他的东西,怎么反倒成了他送给自己的礼物,但她沒有去询问其中的缘由,就像她弄不明白汪春为何要把别人贿赂他的东西告诉李炎一样,有些个人和事永远是那么难以捉摸,
……
绥州刺史府大牢,深夜,
文兰双手被缚吊在半空,武曹挥舞着皮鞭狠狠地抽打着,为了防止文兰凄厉的惨叫声惊扰四邻,武曹在他嘴里塞进了一条十三娘用过的亵裤,
这无疑是对文兰的极大侮辱,身为阶下囚,文兰只有听天由命的份,但让他愤愤不平的是有能力解救自己的薄仲彦,此刻竟也是一副无动于衷、幸灾乐祸的架势,
武曹本來已经答应释放文兰回长安,坏就坏在文兰的一张臭嘴上,在武曹给他摆的压惊宴上,喝的醉醺醺的文兰,搂着武曹的脖子喷着酒气说:“十三娘以后就归你了,兄弟我是无福消受了。”武曹当时就翻了脸,掀了桌子大骂而去,
随后文兰就被稀里糊涂地带到了这里,若不是薄仲彦及时赶到,今天所受的就不仅仅是这四十皮鞭这么简单了,据狱卒们说,就在自己说错话的当晚,刺史府的后院就传出一个女人的凄厉的哭喊声,有人说那是武曹鞭打十三娘的声音,也有人说武曹把十三娘吊起來用针扎她的肌肤,一共扎了七百八十多次,
不管是哪种说法属实,文兰现在对武曹已经是怕到了骨子里,这个满脸阴气的年轻人他现在哪怕是看一眼也会心惊胆颤,
武曹打了四十鞭子,额头就见了汗,他手臂有些酸麻,气喘的也有些不均匀,他摔掉了鞭子,恨恨而去,薄仲彦就在身边,气头上他可以对他不理不睬,但气消了该顾的面子还是要顾的,薄仲彦示意士卒抽出塞在文兰嘴里的东西,
文兰竟“哇”地一声哭了起來,四十鞭子打的他遍体鳞伤,看着很难看,但绝沒有伤到筋骨,薄仲彦鄙夷地看了他一眼,满脸的不屑,文兰抽搭了一阵,龇牙咧嘴地责问薄仲彦:“你明明能救我,为何袖手旁观,
薄仲彦冷笑道:“这是他的地盘,客随主便,我能说什么,他能放你一马,你就知足吧。”
文兰气的浑身发抖,发狠道:“此仇不报非君子,我迟早要砍下他的人头。”
薄仲彦冷哼一声,武曹敢这么对付文兰,除了他性格中的阴狠、残忍,主要还是他看准了自己不会因为文兰而跟他有任何不愉快,薄仲彦刚刚帮武曹收编了文兰旧部,即驻守绥州的三千神策军,仇士良给他的指示是扶持武曹自成一家,使绥州成为关中和丰州、夏州的缓冲地带,仇士良肯做出这样的让步,自然是有他的考虑,
半个月前,剑南黎州历书县饥民暴动,官府无力弹压,遂请求当地驻军协助镇压,驻军出动三个旅入历书县弹压暴民,不想三百名军士竟临阵倒戈,与饥民站到了一起,愤怒的饥民攻占了县衙,抢夺了一个军械库,随即一千名由饥民组成的土军又趁机攻占了黎州城,他们夺取粮仓,开仓放粮,他们捣毁公署,逮捕官吏,黎州官、军、地主、富商纷纷奔命,
黎州暴乱之后,临近的眉州、雅州、嘉州等地,也相继爆发民变,饥民组成武装焚毁官署,抢占仓粮,驱逐官吏,剑南南部地区全部落入暴民之手,,
四州饥民抢夺军械库,组织军队,号称“荡寇军”,他们又与当地蛮族结盟,相约共同抗拒官军,剑南屯兵十万,光成都府就驻军一万,“荡寇军”兵力不过三五千,且都是沒有经过训练的乌合之众,此时官军若进兵剿灭,胜算很大,让人不解的是四州全部陷落后,驻军竟视若无顿,听之任之,
这十万士卒多半是剑南本地土著,他们与荡寇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进剿时刻表一推再推,终至尾大不掉之势,
剑南原本是刺马营的地盘,大明宫变后仇士良的势力开始渗入,一度曾占据了上风,但这两年刺马营的势力在迅速回升,剑南的局势已经处于一种互有攻守的胶着状态,此次饥民暴动,幕后的主使就是刺马营,他们的目的是彻底夺回剑南的控制权,仇士良自然不肯轻易放手,他要集中精力与刺马营争夺剑南,就只能暂时对北方采取守势,绥州他可以丢,但不能丢于杨昊之手,否则至少在表面上他就被刺马营压了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