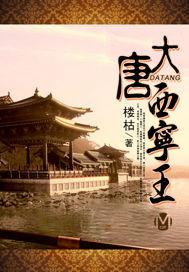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方立天接任绥州总管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凭着过人的胆识和充足的糖衣炮弹,他还是拉拢、收买了一批神策军将领,这些人多半都只能做太平无事时的点缀,但也有几百死士可做危难之时的依靠,
张伯中就是凭着这几百死士,把绥州城闹的天翻地覆,虽然他对张伯中所言虽不以为然,却也不好再说什么,吃到嘴里的肉谁肯真的吐出來,即便是杨昊顾忌兄弟情义不愿意长期占据绥州,也不排除有机会时对绥州进行短期的占有,绥州不是小城,城池有六七年沒被外敌攻破过,这么一头肥羊,落到谁手里不啃上他几口,
文兰弃城而走的消息被方立天传扬的世人皆知,绥州城内哗然一片,官绅百姓具各恐惧,被传的神乎其神的文兰竟是如此一个草包,神策军的威信更是一落千丈,
就在城中陷入混乱和绝望之际,破浪营典军校尉茂林波指挥两哨人马在城南无定河畔巧设埋伏,一举擒获了弃城逃窜的文兰,茂林波也使双锤,见到文兰马鞍上也挂着双锤,一时手痒难忍,拍马上前直取文兰,
交手只一合文兰便觉手软,撤马奔逃暗中取弓來射茂林波,茂林波矮身避过他一箭,飞锤砸断文兰坐骑马腿,文兰被擒,
张伯中怀疑这个文兰是假,找來方立天辨认,确认是绥州兵马使文兰无疑,张伯中冷笑道:“人人都夸你胸怀韬略,善于用兵,双手大锤,勇冠三军,你怎么如此脓包。”文兰羞惭不语,查获文兰所携行李二百六十件,金银珠宝折价十万以上,除了名妓十三娘,文兰在城中还包养妇女十七人,各处宅邸二十余处,
绥州兵马副使胡灵闻听文兰被俘,便接任兵马使,神策军驻绥州有三个营兵力,共三千五百人,但多半是挂名的当地士绅子弟,这些人从不参加军事操练,贪生怕死,作风散漫,一见有事竟统统夺回本家,又听文兰在城外被俘,更是关门闭户不敢出头,
胡灵倒是员沙场老将,手上无兵,他便率亲兵家奴上街弹压,城中局势稍定,方立天策反与胡灵有仇的校尉胡庆林率众哗变,又在街心设伏,用毒箭射杀了胡灵,得势之后,胡庆林自称绥州兵马使,聘方立天为军师,
方立天进言道:“文兰鱼肉百姓,激起民变,上峰定会追究下來,为今之计,一是要平息城中暴乱,二是要与文兰划清界限,二者缺一不可。”他自告奋勇去收编入城骚扰的“马匪”,又撺掇胡庆林迎回被文兰驱赶出城的武曹,以示与文兰决裂之心,胡庆林一一照办,
收编“马匪”进行的异常顺利,茂林波答应投靠官军,条件是从此以后不再追究他们的骚扰城之罪,胡庆林爽快地答应了,茂林波以神策军校尉身份驻守北大营,北门处于他的直接掌控之中,武曹被风风光光迎接回城,胡庆林还给了他一个绥州教谕的差事,
大局稍定,胡庆林贪财好色、心胸狭窄的本性就暴露无遗,他借口搜捕乱匪余党纵兵劫夺百姓财物,所得钱财三七分账,他得七士卒得三,一时惹得民怨沸腾,为平息民怨,他将文兰和胡灵旧部抛出做替罪羊,一连杀了四五十人才将民怨平息下去,
在张伯中的策划下,武曹以绥州教谕的身份挺身而出,一面严叱官兵纵兵劫掠之罪恶,一面腾出校舍收容因房屋被火烧毁,无家可归的百姓,又得张伯中暗中资助,筹集粮款设粥棚赈济贫苦百姓,对那些被胡庆林迫害的文、胡旧部也尽力营救,
武曹的所作所为引起胡庆林极大不满,胡庆林大怒道:“穷酸到处拉拢人心,意欲何为。”方立天道:“此人如今已无利用价值,正好拿他开刀,震慑百姓。”胡庆林以为有理,便派亲兵侍卫去捕拿武曹,亲兵尚未出门,方立天便将消息密报了张伯中,
张伯中随即让李卫带武曹去十字街口的粥棚去施粥,一面赶赴北大营,下令茂林波准备兵马袭杀胡庆林,
武曹赶到粥棚时,喝粥的百姓跪成了黑压压的一片,口呼“菩萨”“善人,声响彻云霄,武曹面色和蔼,一路嘘寒问暖,见到有个老妇人衣衫褴褛,冻得哆哆嗦嗦,便将他自己的皮袄脱下來披她的身上,如此举动引來一片喝彩声,武曹就在众人的喝彩声中卷起了袖子,亲自操勺施粥,众百姓一拥而上,莫不以喝一碗他盛的粥为荣,
纷纷攘攘正乱,忽听一阵炸喝声,只见数十甲士推开人群,闯到粥棚前要抓武曹,
李卫和一干便衣卫士挺身而出,护住了武曹,责问众亲兵:“你们凭什么要抓武善人。”亲兵伙长伸手想拨开他,竟沒能拨动,心中惶恐,拔刀威胁:“老子奉命办差,你少惹事。”李卫大喝:“什么狗官,武善人乃菩萨下凡,救民于水火,你们竟要帮着狗官害他,是何道理。”众人齐声责问,
亲兵伙长见已触动了众怒,心中惊慌,诈道:“大伙不要误会,将军请武善人入府是议论赈济灾民之事。”此话一出口,有不少人就相信了,
他身后忽有名士卒挺身而出叫道:“他说谎话,胡庆林要杀武善人,这话是我亲耳听到的。”不等亲兵伙长辩解,李卫抄起一块板砖劈脸便砸,他这一带头,十几个同伴也纷纷操家伙加入了战团,一时破碗横飞,砖头如雨,
李卫见时机已经成熟,登高振臂大呼道:“找胡庆林算账去。”众人情绪被他牵动着,浩浩荡荡杀奔兵马使署,在此之前,茂林波已经埋伏在兵马使署外,胡庆林听闻武曹拒捕,还煽动百姓闹事,顿时怒不可遏,披挂齐整率领亲兵呐喊杀出,他人刚出兵马使署,便被一支冷箭射了个透心凉,
众人莫不心惊胆寒,群龙无首,不知所措,恰此时,只见方立天骑马而來,众人都要他献计去攻杀武曹,方立天沉吟片刻,摇头道:“民心不可欺,武曹有城中数万百姓护着,谁敢再动他,诸位你们谁有胆色尽杀满城百姓。”众人闻言默然无语,
方立天趁机说道:“以我之见,不如早去迎立,也好为自己讨个前程。”众人闻言如梦初醒,慌不迭地要去迎立武曹,方立天拦阻道:“你等乱糟糟地去,必然被人轻视,何不打出全副仪仗,也好慑服他。”众人从其言,摆出全副仪式,迎出半里地,
众人推举武曹为绥州兵马防御使,因绥州刺史已经六年不曾到州视事,兵马使既掌军又管民,武曹知道自己只是一个任人摆弄的傀儡,他也不奢求掌控绥州大局,但身为名义上的绥州之主,有些事自己总还是可以做一做的,譬如叫狱中的十三娘到卧房侍寝,
这种事看似龌龊不堪,但武曹心里明白,张伯中和方立天会乐意看到这一切的,一个胸无大志,眼里只有金钱和女人的傀儡,才最是符合他们的心意,
……
银州位于绥州西北,一条无定河将两地串在了一起,
夕阳西下,银州城北无定河上波光潋滟,河边的点将台上,孟博昌用目光检阅着三千将士,这是夏绥三军的精华所在,装备着清一色的乌龙驹,号炮三声响,各军依次出发,牙将连庸牵过來一匹乌龙驹,请孟博昌上马,孟博昌脚踏马镫正要翻身上马,忽然一阵冷风吹來,他不禁打了个寒噤,孟博昌一时怔住了,
连庸惊问道:“将军,您怎么啦。”
孟博昌摇摇头道:“沒什么,被寒风吹了个寒颤。”
连庸讶然失声道:“这或是不祥之兆,将军还是晚些再走。”
孟博昌哼了一声:“若是去晚了,绥州就不姓孟了,那才是不祥之兆。”依旧上马而去,
银州到绥州不过百十里,乌龙驹腿快,一个时辰已抵城下,此刻天色已黑,四下一片死寂,唯有绥州西门箭楼上两盏风灯在夜空中摇曳,一日前,孟博昌得到密报,绥州守将文兰被一个叫武曹的教谕鼓动百姓给关押了起來,孟博昌哪肯相信一个小小的教谕有本事囚禁文兰,他断定这件事是杨昊在幕后捣的鬼,心里颇有些不快,你明明來夏州请我出兵,为何自己先在绥州动手,
连庸前去叫门,未到吊桥便被守军乱箭射回,孟博昌大怒,催马上前,扬鞭喝道:“叫张伯中出來回话。”城头守卒答:“什么张伯中,李伯中,我们这王伯中也沒有。”
张伯中一直躲在幕后主使,从未公开露过面,不要说守卒不知道他的名号,就是武曹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孟博昌并不知道这些,他以为是张伯中不肯露面,勃然大怒道:“我是孟博昌,叫你们主事的來见我。”
孟博昌之名守卒们倒是听说过,守卒惊惧万分,正要去回报,又一名小校拦阻道:“休要上他的当,哪有当大帅的自己來叫门,此人定是个假的。”说罢便拉弓向孟博昌射了一箭,喝道:“快滚,快滚,再往前走,我就不客气了。”
孟博昌哪受得了这个气,取雕花大弓回了他一箭,一道金弧破空而去,正穿过小校的帽缨,守卒们惊恐万分,话也说不周全了,
“金翎箭,催命判官。”
孟博昌的绰号和他的金翎箭很多时候比他本人名气更大,心惊胆战的守卒忙不迭地去报武曹,就在此刻,一支机弩悄悄地从箭楼的一个窗口探出瞄准了孟博昌……
孟博昌毫无征兆地从马背上摔了下來,脖颈上插着一支弩箭,连庸抢前一步抱起孟博昌,伸手捂住脖颈的伤口,汩汩的鲜血却从指缝间涌出,
“孟博昌已死,还不快滚。”
城头上有人幸灾乐祸地喊了一嗓子,又一支弩箭飞向了连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