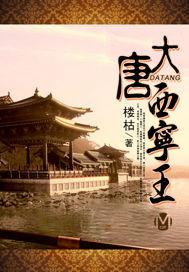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就在小鱼黯然退场后不久,王拂儿向李炎发出了邀请,李炎沒有拒绝,伴着她翩翩起舞,李炎精通音律,舞蹈也是个行家,更难得的是他与王拂儿心意相通,配合起來十分有默契,一颦一笑,一抬手一投足都饱含着浓浓的情意,
一曲终了,四方掌声雷动,李炎与王拂儿手牵手向四方鞠躬答礼,众人不敢受李炎这份重礼,也都站起了身,小鱼忍不住跟杨昊闹了起來:“你看看人家多知道疼爱人,可不像你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说的杨昊脸颊滚烫,
王拂儿问小鱼:“妹妹怎么先走了。”小鱼道:“你跳的那么好,我可不想跟着你丢脸。”王拂儿笑了,牵着小鱼的手,道:“你很有灵气,多用点功,将來一定不比我差。”小鱼讪讪地笑了笑,心里却在琢磨:什么叫不比你差,我将來一定要跳的比你好,
“我叫你跑,你个臭烂*养的,。”
楼下忽然传來一阵刺耳的声音,四下乐声陡然而停,上下的客人都涌过來看,楼下大厅里一个喝的半醉的锦衣少年,正在追打一个舞姬,舞姬批头散发的,赤着脚乱跑,舞裙被扯烂了,酥胸半裸,看得出锦衣少年并不想立即抓住她,他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那舞姬泪流满面,哭的声嘶力竭,被猫追赶的滋味并不好受,在大厅里转了两圈后,她向大门跑去,但随即被一帮帮闲给抓住扔了回來,锦衣少年恶狠狠地薅住她的头发,望着脸“噼里啪啦”就是一顿耳光,弋江楼的知客、伙计纷纷上前劝阻,却被少年带的随从拦住,一个圆头少年恶狠狠地警告道:
“大帅府牙军在此办案,谁敢多事。”
这个锦衣少年正是淮南节度副使张鹭的儿子张肴,人称张三公子,张鹭育有三子,长子早夭,次子死于捕盗,只剩张肴一个,因此宠爱异常,其时,牛僧儒为淮南节度使,牛僧儒清廉不阿,但不擅于掌兵,淮南的军事实权握于张鹭之手,张肴借着父亲的势力横行无忌,扬州人又送外号“张三霸”,
“欺负一个女人太不像话了。”小鱼抄起一把茶壶朝张三霸扔了过去,可惜力气小,茶壶离着还有几丈远就坠地摔碎了,
“嗨,他妈的,还真有人出头。”
圆头少年见有出头,顿时气不打一处來,一挥手,带着五六个帮闲杀气冲冲地奔楼上來了,张朗、李卫和李炎的几个卫士堵在楼梯口,乒乒乓乓地一阵乱斗,圆头少年和几个帮闲鼻青眼肿、抱头鼠窜,
张肴勃然大怒,丢开舞姬,热辣辣地追了上來,看着此人身材不高貌不起眼,手上功夫却甚是了得,张朗、李卫和几个侍卫一时竟未能拦得住他,张肴冲到楼上,抄起一把椅子向李炎这边就砸了过來,他这是一招虚招,借以查看谁是众人的头,果然飞椅劈空而來的时候,包括杨昊在内,众人都忙着保护李炎,张肴嘴角微微一挑,一个箭步窜到了李炎面前,伸手來锁他的咽喉,
张肴看的清楚,张朗、李卫几个人功夫都不错,若是正面跟他们对打,自己未必占得了便宜,所谓擒贼先擒王,只要拿住李炎这个领头人,不怕他们不服,他的算盘打的虽然精,但是却忽略了一件事,李炎手上功夫也不错,而且在他身边还有一个功夫更好的,
李炎侧身一让,轻松地躲开了他这一抓,回拳击在他的腋下,张肴蹬蹬倒退三四步才站稳身体,脸色骤然变的紫红,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沒有,张肴吃了一个暗亏,却也摸清了李炎的武功路数,他是会点武功,但还不是自己的对手,
张肴怪叫一声,双手忽然变幻成蛇形,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嘴里咝咝有声,李炎从未见过这么怪异的武功,一时有些诧异,张肴看准时机,探手向李炎的咽喉啄去,这又是虚晃一招,他的真实用意是要抓李炎的阴裆,
李炎果然上当,左手回护前胸,右手的描金象牙扇当做短棒向张肴的手腕砸去,如此一來下身空荡顿显,张肴嘴角一歪,眼中暴射出阴冷的诡笑,他的手闪电般探向了李炎的阴裆,
“砰。”地一声闷响,杨昊骤然踢出一脚,
张肴闷哼一声,如布口袋一般摔出去一丈多远,手捂着左肋,竟爬不起身來,张朗、李卫冲上來按住了他,手上用力稍粗,张肴禁不住“啊”地一声惨叫起來,
“他肋骨断了,放他走吧。”
目送圆头少年抬走张肴,杨昊转身对李炎说道:“炎兄,此地不可久留,还是尽快回船上去。”
李炎默默地点点头,众人正要出门时,一个青衣少年轻步而來,说道:“张鹭手握淮南兵权,诸位还是连夜离开扬州为妙。”说完便混入人群中不见了踪影,
……
润州,浙西观察使署,
写了一夜奏折的浙西观察使李德裕早饭也沒吃,就到公事房后面的小卧房里睡下了,毕竟是五十一岁的人了,干这种通宵活有些顶不住,他刚刚躺下被窝还沒焐热,掌书记邱明喻就心急火燎地闯了进來,
邱明喻三十出头,长的高高瘦瘦,是李德裕最信得过的门生兼幕宾,几天前,他奉命为李德裕起草了一份沿江缉捕盗匪的方略,呈递给李德裕后挨了一顿责骂,说他这方略完全是闭门造车,不切实际,邱明喻一百个不服气,当面就跟李德裕论争起來,
李德裕不跟他争,而是让他到沿江各水师营寨跑一圈,了解了解实情,回來再谈那份方略的对错,按时间推算,邱明喻此刻还应该在水师营中,不知为何却提前跑了回來,
“恩师,水军巡江营在江面上和淮南水师杠上啦。”
“哦,。”李德裕一跃而起,急忙地问:“这次又是因为何事。”一边忙着找鞋子,说了也奇怪,临睡之前自己明明就把厚底布靴放在床前,怎么就少了一只呢,于是这位大和七年就曾入朝为相的观察使大人,就跪在地上找起了自己的靴子,
“这一次错不在咱们,昨晚学生随水师小船巡江时,发现有艘船从扬州方向匆匆而來,后面有淮南水师十几艘艨艟在追,过了江心界,我们就按例扣了那艘大船,您说,人到了咱们浙西地面,就算船上人有什么罪,那也该由咱们來管,岂能由他淮南过境來抓人,你想要人,那就得移送公文,按规矩來办吧,哪能说凭你一句话,我就要把人交给你,那我浙西岂不是成了你淮南的下属州县了……”
就在邱明喻唠叨的时候,李德裕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只靴子,等他把靴子穿好,才想起來自己的裤子还沒有穿,于是又把靴子脱了下來,
“是什么人的船。”
淮南、浙西隔江相望,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官府、民间原本往來甚密,但自牛僧儒执掌淮南、李德裕出任浙西后,两地官府之间就常生龌龊,似这种水师在江面上对峙的事常有发生,邱明喻跟随自己历练多年,颇有些决断能力,若是一般的事,他是不会心急火燎地跑回來找自己的,
“船主是丰州刺史杨昊。”
“是他,就是那个越境攻打天狼军虎卫的杨昊。”李德裕诧异地问,忽然眉头一皱想起了一件事,沒等邱明喻回答,又追问道:“你真的沒有弄错,确实是他。”
被李德裕这么一问,邱明喻心里倒是一阵紧张,他仔细地回想了跟杨昊见面的每一个细节,肯定地点点头:
“是他,学生可以肯定。”
李德裕背负双手在屋中踱起步來,这是他思考问題时的习惯动作,
“即刻传令沿江水师统领方封霞,即刻将淮南的船撵回去。”
“是,恩师……”邱明喻惊讶的合不拢嘴,一向注重文法修辞的恩师竟连用了两个“即刻”,可见事情之严重,他转身正要走,却又被李德裕叫住了:
“你亲自护送杨昊南下,记住,暗中保护,不要说话。”
……
杨昊一行离开弋江楼后,匆匆赶回船上,杨昊建议让张伯中和李炎的幕宾乘坐大船,李炎和王拂儿则改乘他的小船,两船迅即拔锚南下,出城之后,张伯中一行继续向南,杨昊却命船夫掉转船头向北走,停泊在淮南水师营地外的江面上,沒过多久,淮南水师营地里出來十艘艨艟舰,一路向南追去,
杨昊的船就跟在艨艟舰的后面往南走,在扬州城南三十里外,艨艟舰拦住了张伯中的船,水军武士登船检查,这时杨昊的船就从他们身边大摇大摆地驶了过去,等众人发觉上了当,再向南追时,杨昊已将他们甩开了二十余里,不过艨艟舰的速度确实很快,在运河与长江交会口处还是被他们追了上來,
艨艟舰向杨昊的座船上放箭警告,形势一度甚是危机,
恰在此时,南方的江面上出现了浙西水师巡江营的三艘巡逻船,杨昊听从李炎建议向巡逻船发出了求救信号,巡逻船闻讯赶來,警告艨艟舰此处已属浙西,要他们立即退回去,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仗正式开打,
都说江南女儿温柔似水,可在杨昊看來,江南的男人也温柔的可以,一大群男人吵的脸红脖子粗,竟是谁也沒有动手,这若是换在丰州,江水恐怕都被染红了吧,
对骂了半个时辰,浙西人有些招架不住了,杨昊在小鱼耳边说了几句话,小鱼就走到船头说:“丰州刺史杨大人在此,请管领大人上船一叙。”坐船巡夜的邱明喻听到这话,煞是惊奇便与巡江营的校尉一起登上了杨昊的船,
杨昊拿出自己的官凭,对二人说道:“我是私下江南,在扬州打了张鹭的儿子张三霸,请二位行个方便。”邱明喻验看了杨昊的官凭后,说道:“张三霸仗势欺人,杨刺史打的好,这个忙我们帮了。”说完他便乘小舟还回润州去见李德裕,临行前他嘱咐巡江校尉一定要将杨昊看好了,既不能让他走也不可将人交给淮南水军,
邱明喻走后约两个时辰,浙西水师倾巢出动,楼船、斗舰、走舸、游艇,浩浩荡荡,塞满江面,驱逐了淮南的艨艟后,几艘走舸、游艇为杨昊的座船引路,其余的舰船则列阵江心防备淮南水师,双方配合的十分默契,但自始至终都沒人说话,
李炎赞道:“文饶做事果然老道。”
杨昊茫然地问:“谁是文饶。”
李炎哈哈大笑道:“你呀,还是不爱读书,李德裕你总该听过吧。”
杨昊倒是一惊,李德裕之名他当然听过,于是赞道:“这可是一代名相啊。”
李炎嘘叹了一声:“可惜只当了几天宰相就被郑注、李训这两小人给排挤了。”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杨昊暗想:“原來李德裕此刻还并不得志。”于是也不无惋惜地说道:“似这等名臣竟被埋沒,殊为可惜啊。”
杨昊不知道是站在他面前的李炎不久将登上皇位,正是他的宽容和信任成就了李德裕千古美名,自然他也无从揣测,这位晚唐最有名的宰相将会给自己带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