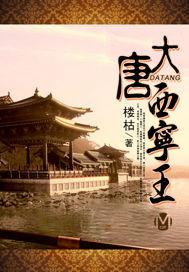.co 在五柳湾休整的这几天,朴恩俊仔细研究了中受降城的地图,这是一份十分详细的地图,详细到城中密如蛛网的小巷和大户人家后花园里的池塘都标识的一清二楚,研究的结果是中受降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王峰不主动弃城,攻下这座山城至少要损失两千名士卒,这对有“爱兵如子”美誉的朴恩俊來说是个不能接受的伤亡数字,这就是他沒有乘胜出兵攻城的重要原因,
不过王赟、王弼兄弟的到來却让朴恩俊看到了希望,二人在城中故旧众多,只要他们愿意进城充当内应,伤亡的数字将会大大减少,
王弼试探着问朴恩俊,扳倒王峰后,他将支持谁为天德军留守,朴恩俊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谁做天德军留后是你们王家的家务事,我等无权干涉,只要肯做丰州的好邻居、好盟友,我们都将全力支持他,这既是我朴恩俊的意思,更是杨大人的意思。”
索额插嘴道:“谁做留后你们可以慢慢商量,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拿下中受降城,我们得到军报,王峰已经向蛮黑部求援,邀请蛮黑部派兵南下助战,蛮黑人相信你们都打过交道,若让他们进城屯驻,别的不敢说,明年此时你们城里必将多出几千个私生子來,上上之计是你我两家联起手來里应外合先破了城,将蛮黑人拒之门外。”
索额这话绝非危言恫吓之辞,参谋司确实八百里加急传來一份军报,指出蛮黑人已派骨朵丽率三千骑兵南下助战,因为是份加密件,他不方便拿來给王氏兄弟看,王弼却因此心生怀疑,当下推脱道:“非是王弼怕死,此次我们刺杀王峰不成,他必防备的紧了,此刻再回去只怕难有建树,反而让他有所警觉。”
朴恩俊闻言也不相逼,就让二人暂居在五柳湾,索额不解其意,问道:“王氏兄弟明明是有办法,却就是不肯帮忙,大哥为何也不逼他们。”朴恩俊道:“王弼是个聪明人,他兄弟丧家而來,手上已经沒有了讲价的本钱,他是想让我们先在王峰那碰个一鼻子灰,然后他再出面帮我们进城,有了这份功劳,再说话他的底气就硬了。”索额道:“这个人鬼头鬼脑的,破了城绝不能让他做留后,倒是那个王赟傻乎乎的好摆弄。”
朴恩俊道:“这些都是后话,等等看吧,或许蛮黑人能帮王弼兄弟改变主意。”索额道:“那受降城的百姓又要遭一茬罪了。”朴恩俊冷哼道:“那也是他们自找的,怨不得我。”
……
为了防备朴恩俊攻城,王峰确实向蛮黑人发出了派兵助战的邀请,本來两家成见颇深,但在钦命天德军巡边抚慰使薄仲彦的斡旋下,蛮老温还是答应了这个请求,在与各家商议之后,便以骨朵丽为主将起兵三千连夜南下,
天德军变乱平息后,蛮黑五部曾随王奔远征奚人,立有战功,后经李载义、王奔、刘沔三人联名保奏,李昂同意划大青山以北、牛头朝那山以东原奚人旧地为蛮黑五部的马场,同时置归原、归化、归诚、归心、归顺五个羁縻州,由五部可汗任州刺史,蛮老唔获赠左威卫将军、归真都督府都督称号,
王峰将三千蛮黑人大部安置在西城门外,一部置于莲花寺西侧,蛮黑人在苦寒之地居住惯了,见惯了数百里不见人影的戈壁草原,乍到这繁华之地,不觉人人心生好奇,士卒三五成群满大街的东摇西逛,见着东西好拿着就走,也不给钱,摊主若去讨要,便瞪眼拔刀,一时闹的鸡飞狗跳,四处不得安宁,
王峰一面与骨朵丽交涉,一面发官榜文告,训令百姓要以大局为重,不得冲撞友军,违者严惩不贷,又派出大批士卒和便衣捕快沿街弹压,凡蛮黑士卒吃喝索拿百姓敢去讨要银钱者,一律以冲撞友军罪论处,轻者责打三十军棍,重则关入大牢,百姓敢怒不敢言,
这一日,两个蛮黑士卒在街上劫夺了两匹麻布,又到街边一家酒肆吃酒,酒足饭饱分文不付扬长便去,店家见二人吃的狠了,也顾不得什么禁令,追上去索钱,两个蛮黑士卒喝醉了,又听不懂汉话,鸡跟鸭话,店主急的直跳脚,这时两个便衣捕快大步赶了上來,抱着双臂,目光阴狠地盯着店主,店主心慌便不敢再动,
两个蛮黑士卒晃晃悠悠正要走,一个瘸腿年轻人提着一根棒子追了过來,叫骂道:“抢布的怛达别走,吃我一棒。”这年轻人名叫少二郎,原是天德军前军的一名伙长,在战场上打瘸了一条腿,回乡开了个钉鞋摊子糊口,他娘五十八岁,瞎了一只眼,在路边摆了个布摊,卖几匹麻布,挣几个小钱补贴家用,
这日少二郎正在修理一只牛皮马靴,有人跑來跟他说:“怛达人抢了你娘的布,还踹了你娘一脚,你娘快不行了。”少二郎闻言飞奔去找老娘,他娘已被邻里救起來,脸色煞白嘴唇乌青,躺在那“哎哟,哎哟”说不出话來,少二郎顿时火起,抄起一根木棒就追了过來,
“二郎莫恼,二郎莫恼。”店主一把将他抱住,小声说道:“这里有两条老王家的狗,你且忍了这口气。”少二郎道:“大叔,这口气如何能忍,堂堂男儿连自己的老娘也看顾不住,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说罢少二郎挣脱了店主,挥棒朝两个蛮黑人奔去,
门口那两个便衣捕快,各丢个眼神,一左一右抄上來,一个抖铁链套住少二郎的脖子,另一个横棒扫在少二郎小腿上,少二郎一声惨叫摔倒在地,众人见他行凶,都躲到了一边,持棒的捕快喝道:“你们这些刁民都听着,谁敢冲撞友军,这就是下场。”众人或惊怖不敢言,或是敢怒不敢言,或是摇头叹息,
这时在酒肆里喝茶的一条大汉跳了出來,此人名唤二狗,是个杀猪的屠夫,见两个捕快行凶,顿时火起,他大步走到使铁链的捕快面前,炸雷般喝了声:“放手。”那捕快吃了一惊,丢了铁链要來拔刀,却被二狗劈手揪住衣领给扔了出去,持棒的捕快绕到二狗身后,跪地一扫,二狗不防备被他扫中小腿,闷哼一声跌倒在地,使铁链的捕快一抖铁链将他脖子套住,狠命地一背,二狗不得不双手抓住链子,咬牙挣扎,持棒的捕快跳身望定二狗的顶门便是一棒,二狗额头中棒满脸是血,顿时昏死过去,
少二郎见自己恩人受辱,胸中怒火难平,一声怒吼跳起來朝使铁链的捕快扑去,到底双腿不济,差了一步摔在那捕快的脚边,他便顺势抱住捕快的腿狠狠地咬了下去,使链的捕快杀猪般嚎了起來,使棒的捕快吐口吐沫搓了搓手,深吸了一口气,举棒望定少二郎的后脑砸去,众人一片惊呼都捂脸不敢看,店主实在看不过去,炸雷似的喝了一声:“不许伤人。”
从后面一头撞过去,将使棒的捕快撞翻在地,二人就在地上扭打起來,店中小二见主人不敌,一个箭步窜上前扯住那捕快的头发挥拳便打,后厨的大厨闻听前面殴斗,围着围裙提着菜刀赶來助阵,
这时在附近巡逻的七八个逻卒围了过來,围观百姓有心维护少二郎、店主等人,挺身将街道阻断,逻卒不问青红皂白挥鞭乱打,顿时有十七八个人受了鞭伤,众人责问逻卒为何打人,一个小校冷笑道:“打你算轻的,老子灭了你全家,你又能奈何。”于是拔出腰刀來,嚷道:“再不滚,全他娘的砍了。”围观百姓见势不妙都有退意,
这时人群中有人怒吼了一声:“反了他狗日的。”只见两个穿草鞋的菜农,手持扁担冲了出去,打的逻卒一个个抱头鼠窜,众人本來就憋着一肚子气,有人这一带头,有人胆子顿时壮了起來,一时间板砖雨点般砸向几个逻卒,那个小校被半截砖头砸破了头,捂着血糊糊的头,扯着嗓子死命地喊:“造反啦,东街的百姓都反了。”
原本街上人并不多,听他这么一喊,都伸出头來看,只见一帮百姓追着几个残兵败勇沒命地逃,众人压抑已久的怨气总算有了发泄的地方,胆大的抄棍子半途去截击,胆小的捡块砖头暗中伏击,孩童拿來铜盆敲打鼓噪,原本只是一条街的骚乱,此时蔓延至全城,
王峰正在牙城宴请骨朵丽等蛮黑将领宴饮,忽闻城中百姓骚乱,一时气急败坏,将牙军将领肖凌夷,受降城巡街使张崇万叫到面前一顿臭骂,喝令道:“酒宴散时,若外面骚乱还不平息,你们两个拿头來见。”二人受了一顿训斥,窝了一肚子火,出了牙署,二人便将这一肚子火都撒到下属头上,下属又去责骂士卒,士卒们便憋着一肚皮气,手持利刃,腰挎弓弩,怒冲冲上街來弹压骚乱的百姓,
牙军士卒和逻卒多是本地子弟充任,为了防止士卒心慈手软弹压不力,肖凌夷与张崇万商议后,让南区士卒去弹压北区百姓,北区士卒去弹压南区百姓,受降城向來有“南富北穷,东商西兵”之说,各区百姓贫富差距较大,平素就相互敌视,此时正好被二人利用,
面对手持刀枪的士卒,街上骚乱的百姓迅速减少,牙军和逻卒见百姓软弱可欺,便肆无忌惮起來,一面残酷镇压敢上街的百姓,一面又以搜捕乱民为名,进门入户敲诈勒索,百姓稍有不顺从,便给你扣上一顶反民的帽子,或当场枭首示众,或绑回去让家人拿钱來赎,
半个时辰后,中受降城的大街小巷再也见不到一个骚乱的百姓身影,街道两边的树上却多了数十颗血淋淋的人头,
肖凌夷、张崇万回牙城复命,此时饮宴已经进入尾声,骨朵丽等蛮黑将领笨拙地扭动着肥胖的身躯,跟那些穿着很单薄的歌姬跳贴身热面舞,
王峰对二人的表现很满意,亲自倒酒给二人,见张崇万面上有些不忍之色,遂冷笑道:“牧民如牧羊,羊儿们不听话就杀他几个,只要杀出了自己的威风,羊儿们就会乖乖听话,毛让你剪,肉让你吃,还会咩咩地给你唱赞歌,子子孙孙都供你享用,不要心慈手软,心慈了,它们就敢心生怨怼,暗中诽谤;手软了,他们就会忘了自己的身份,上蹿下跳,聒噪个不停,说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甚至还要跳到你的头上拉屎撒尿,你们说,是骑着羊好,还是要羊骑着你好,……”
王峰确实喝多了,骨朵丽等人还沒走,他就捡了匹体态丰满的肥羊,把她的肚皮当做枕头,呼呼大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