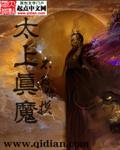.co 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张潜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何意。
然而数十年的相处,他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对父亲所言的每一句话都必往心里去,虽然老人性格有些古怪,然而神志却十分的清楚,一言一行自有他的道理,此刻无端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加上之前那种茫然又偏于凝重的神情,让张潜心头也笼罩了一丝阴霾,轻声问道:“谁来了?”
“你附耳过来。”老人微微摆了摆手。
张潜越发觉得狐疑,举目看来看门外,一片风雨却无半个人影,但还是依言做了,躬下身去。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老人让他附上耳来,而后张嘴念出一段经文来,这声音虽然有气无力,然而每一个音节都像洪钟大吕一般,从耳中灌入心间,一时间体内体外皆是这声音,连一步之隔的风雨都听不见了。
“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化定基。”
如今正直道宗年间,天下敬道门为天地之师,道学昌盛,连书院之中都要学《道德》《南华》等经,而世间仙术更是以此为源,因此更受人追捧,张潜耳目渲染自然也有所知,虽然这段经文有诸多不解之处,然而立意观点他却能听的明白,与道德之文相去甚远,却也不能说相互矛盾,只是立意背道而驰。
道德经有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此为大道,又有言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因此人在大道之前因心存敬畏,而人修仙以求长生,也是追寻大道,然而这断经文之中,种种所言,诸如执天之行,施行于天,确实将人与天道并存,甚至凌驾之上,观其言知其意,不觉骇然。
对于人所言之的大道,张潜并无太多敬畏,因此也不觉得这经文太过大逆不道。
他更在乎的是眼前日子,简单倒衣食住行,迎来送往,一个整日为生活操劳的人是没有那闲工夫揣摩那虚无缥缈的东西的,他不知道父亲给他念这么一片经文所谓何意,然而听到后面“性有巧拙,可以伏藏”那一句时却忽然觉得有些熟悉,心中一忖豁然开朗,这正是父亲当初所授武经中的一句,亦是其主旨。
“以此为主旨融合《灵枢》《素问》二书之言,正是那套武学的由来!”张潜心头琢磨,不由讶然。
这篇经文通篇所言有四百余字,父亲之前所授武学仅仅只是其中一言,为锻炼皮肉之术,而往下继续推敲,还可衍生出更深层次的东西,诸如筋骨、脏腑、血髓、穴窍的练法,只是如今时间紧迫,张潜也只能看清一丝轮廓,想要将其中法门完全推敲出来,不仅需要揣摩,恐怕还需他一步步走至那种境界才能领会。
“以此经为骨,以灵枢素问为血肉,自可衍生无上法门,此法名:道渊!”
张九德解释一句,却不知张潜早已看透其中玄机,而后一字一句的说道:“切记,法不传六耳。”
张潜隐隐觉得《道渊》之名颇有深意,然而此时风声鹤唳、山雨欲来,也没有时间细细推敲,而后没等他点头,张九德已经将手轻飘飘的探出,形似槁木抽枝,然而速度快到张潜都未能察觉,便觉那指尖已经点到自己胸腹正中线、脐上六寸之处,正是巨阙穴所在之位,主藏肺腑之潮气,募送心经气血。
医理之中便是如此而言,若是通俗解释,此穴位的作用就是将人食五谷之精微转化为气血。
若遇饮食失调,五谷转化不畅,生胸闷、呕吐的症状,针砭此穴有奇效。
张潜不知道父亲为何突然来此一手,但却没有抵制,也是无能为力,他自以为习武数年之久,力气、速度都要快过寻常人许多,然而在张九德面前,就像是被放慢了一般,眼睁睁的看着那枯槁的指尖点到自己身上,那一层单薄的麻衣顿时被穿透,而后觉得一阵疼痛,如遭雷噬,浑身上下使不出一丝力气来。
而后便觉一阵暖流自痛处蔓延开来,那巨阙穴内的气血竟然旋转起来,如同涡流一般。
初逢此变,张潜只觉得恶心想吐,而后歇上几息时间,又觉得腹中一空,饥饿难耐,然而浑身气力却莫名强了几分,正是那巨阙穴突生变化所致,张潜熟知医理自然不觉奇怪,只是不知父亲用何种手段,竟然使得自己这巨阙穴的生理机能比以往强了数十倍,这种手段简直堪比自然造化,近乎于仙!
张潜先前被一下点中巨阙穴,瘫坐在地上,此时慢慢回过气来,抬起头看去。
只觉得张九德那熟悉无比的模样此时看在眼中竟然极为的陌生,这还是自己所熟知的父亲吗?
他突然想起了今日杨继业与他所说的那番话,此时想来却觉得这厮眼光真是毒辣,连自己一直都被蒙在鼓里,然而却被他看透了一丝玄机,还真应了当局者清旁观者迷那句话,然而他此时根本没有心思去想什么前因后果,也没功夫长感叹这世事无常,数十年的平静至此打破,绝非父亲一时兴起。
显然有事情发生!
张潜并不知道自己随父亲迁来这古庙村是何时、何因。
但是自从知事以来,张潜行走人世之间,见过无数家庭,两相对比之下,不难发现自己父子二人与旁人的不同之处,只是不想多问,父亲对过去一言不提自有他的道理与苦衷,他却是一个明白人。
然而此时观父亲言行举止、神色情绪,张潜心头有些猜测。
父亲携自己隐居此处,恐怕是为了避祸,至于此祸具体是指什么,他却是不知。
“可曾记住?”张九德复问一遍,自然是指他先前所言。
张潜点了点头,一拂身上灰尘,站了起来。
“记住便好,你且离去,勿回此地!”张九德言语简单,却不容辩驳。
眼下之境,虽然还是风平浪静,甚至毫无显迹,然而张潜却已经感受到了那种扑面而来危机,根本不需要张九德一番危言耸听来说服他,只是心头仍放不下,毕竟在他眼前是朝夕相处十几年的父亲,怎能丢下他孑然一身而去,双拳紧握、眉头微皱、一语不言,半晌也难作出决定,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
“当你无法改变这个结局的时候,你就要试着去接受,因为只有接受之后,你才明白如何去反抗!”张九德怒斥一句,神色之中隐现焦虑,而后抬眼一看天边,虽未睁眼,却似了然。
神色之中更多了一分凝重。
张潜自知先前荒唐草率了一些,也不再多言,顿首拜道:“孩儿拜别父亲!”
未等他说完,张九德忽然伸手,在虚空之中连连勾画,转瞬一道符箓凭空而成,四周寒风涌动,那符箓似细线连着的风筝一般,飘摇不止,而后见他指尖一顿,那符箓顿时打在了杨玄后背衣襟上。
“去罢!”张九德轻斥一声,而后抓着张潜背后衣襟,随手一扔。
张潜只觉得被一股沛然莫御的力量扫中,整个人似稻草一样飞起,未等他定住心神整个人已经在山崖之上,那破败的小庙在风雨之中逐渐模糊,敞开的破门中还有一丝烛火传出,隐隐可见其中枯坐的人影,张潜眼眶有些湿润,却被风雨迷了眼睛,在看不清那熟悉之处,便也罢了,收回目光打量起周遭环境。
这一看顿时心惊,只见自己悬于虚空之中,身下便是怪石嶙峋的山坳。
张潜没料到父亲这力气竟然如此恐怖,简直不像常人,随便一扔竟然将自己甩出了几十丈远。
父子二人曾经居住的古庙在那半山腰上,山势虽然不算陡峭,然而这般摔进山沟里,必然有死无生,没等他缓过劲来,只觉得一阵狂风凭空而生,将自己团团裹住,彻骨的寒冷弥漫全身,四周风雨迷茫,就像一个厚厚的茧子,一股无孔不入的气流让他呼吸都显得无比困难,而后觉得身受巨力冲撞,近乎散架。
风雨之中,一道白浪破空而去,犹如陨石一般,将那遮天的雨幕都撕扯出了一个滴水不入的甬道。
狂风逝去,天地间才恢复片刻平静。
须臾之后,天边又有乌云压来,丝丝细雨转瞬连成一柱,又过一两个呼吸,便似瓢泼。
风雨之中似有一人自天边而来,脚下如踩天梯,一路所至之处,风雨避让雷电虬结,犹如神迹。
而那人的脚步始终不紧不慢,雍容而淡定。
他身穿山川河泽紫绶仙衣,齐肩圆领、大襟阔袖、长可及足,束金镶玉嵌东珠带,头戴紫金镂云纹盘龙高冠,眉目间秉承了无尽的荣华与威严,狂风暴雨都无法将他身上沾湿一丝,亦或是掀起一片衣角。
仿佛这人走到哪里,就是这一方天地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