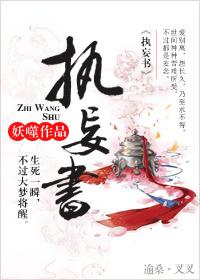.co 所以说习惯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东西,同样可怕的还有女人的直觉。
风寂抹去了叶澜音的记忆,抹不去的是她和苏越相处的那两年的习惯和动作记忆。譬如叶澜音喝的茶总是苏越递给她的,不烫,却又比温暖还要热乎一些。她醒来后在琼瑶山上明明也找了青凤髓来泡,却怎么也拿捏不准那样的温度。又譬如她将那些原本种下戌晚花的花籽拿来种白菜,会在一边翻土的时候一面朝自己身后说话,她怔了一会儿回过头,才发现自己身后空无一人。
醒来之后她莫名其妙的多了一颗心,而那颗心却又空落落地疼。
后来有一日她坐在院子里,折了一只桃花在手中把玩,一只青鸟拖着大尾巴落在叶澜音的肩头,拿喙去啄落在叶澜音手心上的花瓣。她曲起手指去挠青鸟的下巴,用记忆中好似熟悉的语气对那只青鸟说道:“我好像忘记了一个人。”
叶澜音也在她问自己。
她忘记了一个人,也似乎忘记了自己。
当叶澜音找寻着那副画卷的感应来到北邙山的时候,她见到那个院子。见到院子里那一株开的正艳的红梅树,见到院子里那一片盖了薄薄一层雪的白菜,她不知所起忽然就潸然泪下。一草一木,一花一叶,比起琼瑶山,这个地方给她的感觉更加的熟悉。叶澜音站在院子里,望着那微微敞开的门,伸出手犹豫了很久终于将它推开。
‘吱呀’的一声,尘埃在阳光中轻舞飞扬,那副画就挂在正厅的墙上,只一眼叶澜音就看见了它。画中有一面沉香木墙,上头开满了梨花,花至荼蘼似一夜雪急落了满枝。簇簇白梨花下摆放着一张黄花梨木的玫瑰椅。原本那张玫瑰椅上还端坐了个美人,锦衣华服柳眉烟目,那便是叶澜音如今的这幅皮囊。叶澜音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她自己的那幅画上,而是落在那副画两旁挂着的另外两幅画上,叶澜音本不懂画,却因瞧着风寂画了上千年的画便一眼能够认出何为风寂的手笔。而那两幅画显然不是,一副画了映着皎皎一轮满月的小潭,浮着深紫色的睡莲,还在一处搭了个四四方方的亭子,四面挂着白色轻容纱的垂幔,中间一个回字露出清澈见底的潭水。亭子四面都立了灯,不过灯芯却燃尽了。
若说这一幅画画的是山水还说的过去,那么另一幅画却显得有些奇怪了,上好的熟宣被表在绢上,画的却是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柜子。叶澜音觉得怪异又更觉得熟悉,便伸手去到那画中抓了一把近身柜子里的东西出来。是一个陶罐子,上头用楷书端正地写了敬亭绿雪四个字。里面装的是茶,于是她又伸手往那画中抓了一把,这下抓出来的是一个檀木盒子。叶澜音对这个檀木盒子简直再熟悉不过了,她甚至不用打开,光掂量掂量就知道这里头装着的是什么。
果然,那里头躺着一支嵌羊脂白玉的簪子。那是她这幅皮囊还在画中时簪在鬓边的一支。叶澜音有从那画中陆续拿了几样来看,皆是她认得的东西,有琼瑶山上的灵药,有她好几件精致的广袖衣裳,有首饰,有零嘴,还有她习惯枕着的一张玉枕。都是与她有关的东西,都在这里,在北邙山而不是琼瑶山。她一定在这里生活过,因为她在这里留下的痕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放下手中的东西,叶澜音心中的疑惑就像是迷雾一般,她侧过头看到房间的一头摆着一张床,床上的被褥铺的很厚也很是整齐,床边还有个炉子,炉子旁有一张小椅子,椅子上垫了块厚棉布上头放了三个汤婆。
“小澜。”
她听见有人这样唤她。温雅柔润的呼唤,如花瓣跌落在小池塘上泛起的涟漪。她本能的带着欣喜的目光转身回头,身后却空无一人。只有被风吹起的帷幔,飘飘荡荡。
那些帷幔的后头,摆着一张铺了白狐裘的塌。左面是一扇窗,正好对着窗外的红梅。右面靠墙处有一个画屏,屏前设有一张翘头案,案上摆放文房四宝、笔洗、笔注、笔筒和镇纸等。案旁还有一张小案,上头摆放着茶具,旁边还有个铜炉。这间屋子余下的空间则全部摆放了长长的架阁,塞满典籍。
叶澜音走过去,那摆放着茶具的小案上还躺着一支红梅,却早就已经颓败了。
青瓷盏中余有三杯茶,一杯在小几上,两杯在翘头案上。小塌上躺了卷半开的竹简,叶澜音拾起来看是一卷琴谱,看样子有些年头了,竹简的颜色都很不一样。叶澜音自己都觉得奇怪,因为不通音律的她竟然还能看懂这卷琴谱。翘头案旁有一个白瓷缸,里头放着画,大多都是裱起来成了卷轴,却有几张只是单拿宣纸卷了放在那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叶澜音抽了一卷出来看,宣纸慢慢展开,映入叶澜音眼前的这张画显然与这屋子里挂着的决计不是一个画风,手腕虚浮下笔深深浅浅,可见是力道也并未把控好。然而纵使画功如稚儿,叶澜音还是能够认出这水墨勾勒的是一位男子。
依稀是同一个男子,有他看书的时候,有他抚琴的时候,还有他煮茶或是小寐的时候。每一张画上男子的嘴角都噙着温润雅泽的笑意,而透过这几张笔法粗糙的画,叶澜音的脑海中竟然也片段似的浮现出一人的样貌来。样貌有些模糊,然而嘴角的那抹笑意与那画中一般尤为清晰明显。
叶澜音的手微微有些颤,她将画摊放到案上,顺势拿手撑着案,用来支撑她的身子。脑袋有些疼,她越是努力的想要看清脑海中那名男子的脸就愈发的疼。
苏绯织火急火燎地赶到北邙山的时候,来不及感叹物是人非便直奔院子里去,他一步跨进屋内,瞧见墙上那幅画时心中顿时了然。苏绯织转头见叶澜音背对着他坐在地上,背上无起伏,想必也没有在哭。苏绯织安慰自己也许是自己想多了,小叶子不会记得苏越,她来这里只是循着那幅画来的。苏绯织一抬手,那画便送墙上落了下来,卷好了落入他的手中。苏绯织堆起笑,使自己的神色看起来一如往常,他想叶澜音走去,笑了两声,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对叶澜音说道:“你若不问我,我倒是忘了这北邙山我与你还是待过几日的。”
只盼小叶子不要刨根问底,毕竟苏绯织不善于,不屑于说谎话,更不愿意对叶澜音说谎话。
然而当苏绯织走进了,才发现叶澜音怀中抱着一张琴。他虽然不知道这琴的由来,却也知道这是苏越斫的一张琴。苏绯织停下脚步,揣着他的骨扇,心中略有些慌,他瞟着眼睛想要去看叶澜音此时的表情,然而叶澜音却开口问了他一句他最不想回答她的一个问题。
“苏越在哪?”
叶澜音的声音压的有些低,听着很没有力气,入耳的是微微有些沙哑的气声。苏绯织暗咬牙,首先想到的是,坏了,这丫头一定是又哭了。其次他才不得不直面这个棘手的问题,同时苏绯织心中又倍感疑惑,风寂不是施法抹去了叶澜音脑海中有关苏越的一切记忆吗,如今她又怎么会问起苏越,她想起了苏越然而又想起了多少?
在一个弹指间,苏绯织在心中问了自己更多的问题。一个弹指前,他尚且心存侥幸,觉得叶澜音问起苏越不一定是她想起了苏越,而只是知道了在北邙山上有苏越这么一个人而已。毕竟北邙山是苏越的北邙山,叶澜音通过这里的生活痕迹找到他的姓名也是极其正常的一件事。然而一个弹指之后,苏绯织便有些颓败和抑郁的亲手将这个满怀着希望的念头给否决了。
叶澜音哭过了,显然只能是因为苏越。苏绯织第一次在心里将风寂骂了爹也骂了娘,然而面对叶澜音他张了张口,却只能喊出她的名字。
“小叶子……”
“我问你苏越在哪。”不问疑问句,而是平淡的有些可怕的陈述句。叶澜音在找苏绯织要一个肯定的答案,是的,她想起来了,想起有关苏越的一切,自然也知道如今苏越已经不在了。
叶澜音怀抱着那张琴,琴身的木料染上她身上的温度,也变得温暖起来。然而当时她那样抱着的苏越,她那样的痛苦,哭泣和哀求,却也只能感受到他在自己怀中越来越冷。她能握住他冰冷僵硬的手,却抓不住他流逝的生命。
苏绯织憋了一口气,直挺挺地伸着脖子,双眼一闭全然一副早死早超生的模样做足了之后。他长长一叹,上前几步伸出一只手欲要拉叶澜音起来,苏绯织又叹了一口气,告诉她:“我带你去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