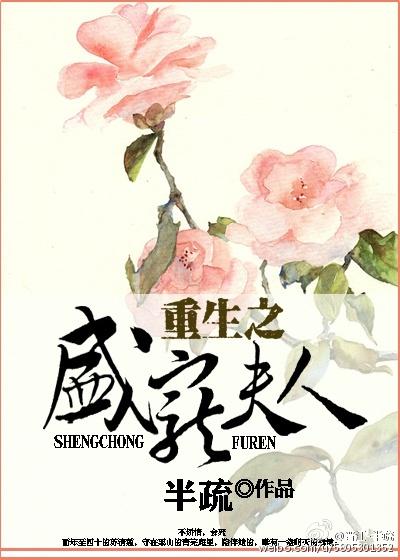.co 苏清蕙想到张刘氏对自己微微的不忿,觉着这一回张家该是不会那般轻易地再为张士钊求娶自己,越发觉得今个真是个好日子。
一时兴起,约了顾彦、吴明兰、莫漪等寒食节的时候,一起去踏青折柳。几个女孩子聊到兴头上,有些难舍难分,干脆一起陪着苏清蕙去书院的客舍见安言师傅。
安言师傅是藜国颇为传奇的才女,生平博闻强记,年轻的时候常和夫婿一起比试文采,两个人收藏了十几间屋子的诗词和金石刻本,只是后来时局动荡,丈夫又早逝,她一个人为了这些书籍、石刻,吃了许多苦头。
安言师傅没有子嗣,连亲近的子侄也折在了战火里,几个女孩子过去的时候,便见着一个有些枯瘦却身形洒脱的老妪在担着水,屋内的灶台里传来霹雳的豆荚爆裂的声音,大家一时都不住红了眼眶。
她们只知道安言师傅动荡一生,却一直不曾见到曾经的官宦小姐、藜国才女,晚年竟需要亲自担水作食。
她们背负着藜国才女的盛名,得到的不过是三两虚伪的遥相恭维罢了。
“清蕙,你怎了?”已是满头银丝的老妇人听着门边的响动,一回头便见着好些日子不曾见到的徒弟正在那里望着她不住落泪,一双剪水秋瞳,水雾濛濛。
放下木桶,召唤女孩子们进来,枯瘦的手拈起丝帕,轻轻地一点一点为徒弟擦拭。
“师傅,徒弟前些日子落水后昏睡不醒,以为再见不到师傅了!”苏清蕙想起这个曾经视她为亲孙女的老人,最后撒手人寰之际,自己竟未能尽孝膝前。
不论是安言师傅,还是她,都不曾因身为才女而幸福过,她们追寻了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
苏清蕙为安言师傅的一生,也为她自己,哭得痛彻心扉。
顾彦、吴明兰都上前安慰,不知什么时候尾随一行人过来的席斐斐习惯性地想嘲讽两句:矫情!可见苏清蕙哭得像没了娘一样,虽觉得怪异,却好歹忍住了。
苏清蕙也意识到自己哭得太过了,接过小姐妹递过来的绣帕,擦了眼泪,有些不好意思地对着安言师傅说:“弟子一时情绪失控,师傅莫在意!”
安言师傅一张布满皱纹的脸笑的沟壑渐深,“你们都是伤春悲秋的年龄,不碍事!”蕙儿扑到她怀里的那一刻,女孩家娇软的身体,让这个老妇人也感动不已,临到老,还有一个这般珍视她的徒弟,也是晚来幸事了。
吴明兰看着平日里和她们讨论诗词歌赋,仿若不沾烟火气的安言夫子,忍不住问道:“夫子,难道书院没有给您配一个使唤丫头吗?”
女夫子微微一笑,“我还使得动,不需要,每日里劳作一会,也能锻炼筋骨,不妨事!”
莫漪眼眸微转,“那我们以后每日下学有时间也来陪夫子锻炼筋骨好了,夫子不知道,这春日里,我每每觉得浑身酸软,课上常不由得昏睡。”
女学生的好意,安言师傅并未拒绝,她这个小院里,也确实有些孤寂,这些女学生正是烂漫的时候,她也喜欢和她们处一块。
这一日里,待莫家、吴家、席家、顾家的马车都接了各家小姐回去后,安言师傅拉着苏清蕙进了内室,摸摸索索地从一个小匣子里取出一封信来,“清蕙,这是我夫家的侄孙给我寄的信,说想接我回去终老,不怕你笑话,我一辈子无所出,即使回去,孤零零的一人,也未必比这好!”
“师傅留在这便好,徒弟一定好好孝敬您!”苏清蕙恳诚地说道,师傅和这侄孙怕是一面都未见过,想到这里,苏清蕙忽觉得前一世她辜负了许多人,包括安言师傅。
安言师傅摇摇头苦笑:“傻孩子,女孩子家一嫁人,可就由不得你喽!”见徒弟张着口要辩驳,安言师傅摆手制止道:“我和你说这个,是有事要托你!”
见安言师傅一脸郑重,苏清蕙也忙端坐好,便听安言师傅说:“我和亡夫花了毕生心血,收集这些金石孤本,待我百年后,自是要妥当归置它们的。你是我唯一的入室弟子,我是准备留一半给你的。”
“至于另一半,”安言师傅摇了摇手里的信,“你到时帮我托付给这位子侄,他现在在蜀地任宣节校尉,好歹也让亡夫后代有一半留存啊!”安言师傅面上不由有些凄凉。
听是蜀地,苏清蕙心里微动。藜国的武官不逢战事,一般会长期驻在一个地方,试探着问道:“不知师傅的这位侄孙,姓甚名谁?”
“我亡夫姓程,这位侄孙名修,字子休!”
苏清蕙“噌”地一下子站了起来,程子休竟是师傅的侄孙,那前世,他为何不曾对她说起?她一直当程子休真的与张士钊有着深厚的兄弟情谊,故此才会在张士钊去世后,对自己百般照顾!
“清蕙,有什么不对吗?”安言师傅见徒弟像受了惊吓似的,有些茫然地问道。
苏清蕙努力压下心头的悸动,尽量平静地说:“师傅,没有什么,这名字我听了好像小时候的一个玩伴,仔细一想,那玩伴不姓程的。”
安言师傅听着徒弟声音有些颤抖,直觉清蕙并没有说实话,见徒弟面色潮红,似有心事,一事也没有就这事多提。
苏家派马车来接的时候,好些人家屋顶已经飘了炊烟,苏清蕙由牡丹扶着上车,一路上脑子一直处于空白的状态。
她曾经陪着张士钊在蜀地待了三年,张士钊任知州,程修任宣威将军,蜀地匪患多,二人时常联手剿匪,程子休一直未娶妻,张士钊常请他过府饮酒畅谈。
她与他的话并不多,苏清蕙忽地想起,程子休是问过她:“嫂夫人是否曾师从安言夫子?”她当时也以为他是客套地询问一句而已,并不曾知晓,她是与他一起接管了师傅的毕生心血。
“小姐,你可是不适?”牡丹仰着头担忧地问道,她隐约觉得小姐今个下学后有些不对劲,额上竟隐约可见淡淡青色的筋络,像是心绪急剧起伏一般。
“没事,可是今日有一阙词怎么都填不好。来,和我说说最近城上有什么趣事不曾?”苏清蕙见牡丹溜溜转的一双杏眼,便觉得灵动有趣,一时也不想去想那些事,这辈子她不会嫁给张士钊,估计,也遇不到蜀地的程子休了吧!
“小姐,有趣的事倒没有,奴婢今天在课间,听其他小姐妹八卦说,大老爷似乎要将湄小姐嫁给东城张家三房的老爷。”牡丹犹犹豫豫地启口道,说完便垂下了头,主子家的事,一向不容她们下人置喙的,只是她知道小姐和湄小姐一向交好。
苏清蕙一时思绪没有反应过来,半晌才恍然道:“你说湄姊姊要嫁给张家三老爷?”
牡丹觑着眼看了眼小姐,钝钝地点头。
苏清蕙只觉眼前无数星星在转,张家的三老爷就是个疯子啊!自称什么青芜隐士,不过沽名钓誉之辈,更重要的是,张家三老爷有个不为人道的暗疾!这事再过个几年,整个仓佑城都会知道的,湄姊姊要是和他订了亲,一辈子可就真毁了!
苏清蕙回家立即隐晦地和爹爹提了这事,只说是小姐妹们在书院议论的,张家三老爷的事,虽然目前并不是都知道,但是苏清蕙隐约提起几句,她相信她爹会去查的!
毕竟清湄和清林是伯娘下辈子的依靠,只要伯娘在,爹爹和娘就会管湄姊姊!
苏志宏的行动力并没有让苏清蕙失望,很快娘便和她说:“你大伯真是鬼迷心窍,竟要把女儿往火坑里跳,那等人家,竟也看得上!”苏侯氏便说便摇头,眼里满是对苏志远的不屑。
苏清蕙隐约觉得,这世的发展轨迹似乎和上辈子不一样,上辈子并没有听过湄姊姊和张家的亲事啊?
可是不管怎样,这事解决了,不仅帮了湄姊姊,便是爹娘在得知张家三老爷那暗疾之后,估计也不会对张家有什么好印象了!
没了前世里的争强好胜,也没了什么歪倒人怀的流言,苏清蕙在书院里过得颇为安逸,每日里听听课,和小姐妹们去安言师傅的小院里帮着缝补衣服、做做饭食,日子过得倒也轻快。
便是一向不对眼的席斐斐也能好声好气地聊两句了,虽然席斐斐有时候还是会炸毛。苏清蕙依然会在第二天当做啥也没发生似的,继续找席斐斐聊天。权当在这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找些乐趣了。
席斐斐是个刺头,书院里和她交好的女孩子寥寥无几,顾彦见苏清蕙有些交好席斐斐,还劝她来着:“她就是一个刺头,仗着是京里来的,谁也不放在眼里,你理她作甚?”
“彦大美人,她就愤世嫉俗了些,心眼也不坏,多个伙伴不好?”苏清蕙笑嘻嘻地看着顾彦,见她嘟囔着嘴,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自个,眼睛里都是一副你忒没骨气的样子,只得收起笑嘻嘻的脸,好言好语地安抚。
其实,苏清蕙是记得的,前辈子她名声那般臭,席斐斐却不曾落井下石过,有一次她陪着张士钊上京述职,在某家宴会上偶遇同样梳着妇人髻的席斐斐,她还讥讽她不争气来着,那神气和眼前的顾彦像了七八分。
苏清蕙和顾彦所在的是书院后花园的花亭,许多学生课间都会过来走走,一会便又有几个女学生过来歇脚,苏清蕙已哄好了顾彦,两人商讨着夏季要做什么式样的衣裙来着,便忽听刚进来的一女学生说:“听说张家公子在议亲了!”
苏清蕙耳朵微动。
另一个女学生说:“是东城张家的公子吗?他不是才考了举人回来吗?”
“对呀,功名有了,所以他娘开始给她挑媳妇了,听说长得挺俊俏的,你们见过吗?”
后面的苏清蕙便没了心思听,张士钊开始议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