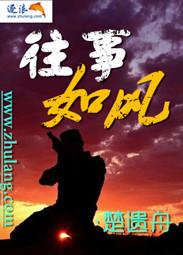林风雨并没有离开太远,她在外面绕了一大圈后,装作漫不经心地样子,走回刘益州的楼下。[燃^文^书库][]
她挑了对面的一个茶馆,坐到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要了一壶茶。
她静静地观察着窗外。
在她果断挂掉打给刘益州的电话之后,她其实还打了个电话,110,她告诉警察,刘益州所在的房间发生了重大案件。
当她在这个茶馆坐定的时候,警车也刚刚来到楼下。
她等待着,心中残存一点希望,希望刘益州陪着笑脸和那几个警察一起从那个屋里走出来,告诉警察们这一切只是有人恶作剧。
但她期待的场景没有出现,林风雨的心沉了下去。
她看到那个窗帘被完全拉开,一个警察的脑袋露出来,在窗口四顾。
这时,另一辆车驶来,几个人拿着担架上楼了。
那是一辆殡仪车!
又过了一会儿,那几个人抬着担架下来了,担架上蒙着白布。
林风雨用手捂住嘴,泪水从眼中流了出来。
她不得不承认,那个胖子,那个有点自恋的、满怀智慧的、满怀爱国激情的上司刘宇州,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设置的那个赌局,输赢还没有定,他却提前离场了。
现在,在这个赌局中,只剩下林风雨了。
她是棋子啊!
还有一个问题,她的档案不在情报部门,外人固然查不到她,她自己也没有办法和情报部门联系了。
从今天起,这就是孤军作战啊…
林风雨平息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找个借口,从茶馆的后门出来,悄悄离开。
“那又如何!”一股豪气从林风雨心中升起,她仿佛面对着刘益州,“那么,上校同志,从这一刻起,我林风雨来来代替你继续着个博弈,唯一不同的是,我既充当棋子,也充当博弈的一方!”
她的步子变得稳健。
她回到家的时候,赵姨依然没有回来,她倒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思考着今后的安排。
越是关键时刻,越是需要冷静,需要沉着地观察。作为特工人员,她当然明白这一点。
现在她明白,这栋小别墅,造型别致,绿树环绕,屋外溪水潺潺,这里宛如人间仙境,但透过这些表面现象,这里也可能是一座人间地狱。
白梦楼,那个外表温文尔雅的绅士,谁也不知道他的内心,谁也不知道他暗地里究竟在干什么?
爱,本来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但他却被爱严重扭曲了,扭曲得近乎变态!
她能做什么?
她有力量做什么?
她忽然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至少,她得有一支枪吧?可是,刘益州没有给她呀!
想到刘益州,她的心中又一阵绞痛。
现在没有人能帮她了,她是个和组织失去联系的情报人员,她只能靠自己。
然后,她想到了莫如风。
她初见莫如风时,还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贩儿,备受欺凌,直到上次在刘益州安排下,莫如风协助她进入书房,她才知道,莫如风其实也在开展着和自己类似的工作。
其实,她不知道,在她和白梦楼举行婚礼的那个晚上,方芳李代桃僵,然后被困火海,最后把方芳救出火海的其实也是莫如风,还有莫怀文。
那一次,莫如风同样是受刘益州之托。
林风雨相信,莫如风有办法给她弄到一支枪!
晚上,林风雨发现,别墅外多了些人。
“现在治安状况不好,亡命之徒越来越多,我们要提高安全警戒的级别,这些都是公司的员工,被安排来保卫我们的安全。”白梦楼淡淡地说,“以后进出这栋楼,都要检查,防止坏人趁浑水摸鱼。”
“这主要是为了你的安全!现在怀着仇富心理的人很多,他们自己好吃懒做,却看不得别人生活好一点,针对富人的偷、抢、绑架案件层出不穷!”白梦楼见林风雨神色不对,接着说。
白梦楼的眼睛隐藏在深色的镜片后面,仿佛看透了林风雨似的。
林风雨不自禁地感觉到一股凉意。
他一定是感觉到什么了,加强了戒备。
那么,后面的事情就更加艰难了!
她感觉自己好像置身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周围的丛林中露出一双双闪烁着绿色光芒的野兽的眼睛,它们时刻都会扑过来!
而她的战友,只有远处那一个模糊的背影…或许只有他可以依赖?
那是莫如风。
此时,莫如风正在医院里,心潮起伏。
非非那天遇到杀手,虽然凭着机智与勇敢逃过了一劫,但被杀手踹了一脚,胸口疼痛。
莫如风带他到医院,医生建议做个全面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腹内少量淤血,需要吃药打针。
但让莫如风震惊的不是非非的病情,而是化验结果上非非的血型!
非非是“o”型血!
而莫如风的血型是“ab”型,根据遗传规律,血型为“ab”父亲的孩子,血型可能是“a”型、“b”型、“ab”型,却绝对不可能是“o”型。
也就是说,非非并不是莫如风的亲生孩子!
对莫如风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晴空霹雳!
从非非出生开始,他对非非就痛爱有加,他看着非非咿呀学语,教他走路,送他上幼儿园…他对非非的爱超出了一切。
而庄晓月对非非反而不那么喜爱。
看着熟睡的非非,莫如风几次想转身离开,但他看到孩子睡梦中露出的笑容,又忍不住留了下来。
在血雨腥风中爬摸滚打,多少次果断地作出决定!而这一次,竟是如此艰难…
非非醒了,他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孩子的世界总是那么单纯。
有莫如风在身边,非非总是很安详。
非非的身体并无大碍,莫如风尽管心中如巨浪排空,但依然冷静地办完了出院手续,带着非非出了医院。
他重新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安置非非住下,并把“小猪”给他带来。
安排完这一切,他知道自己该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