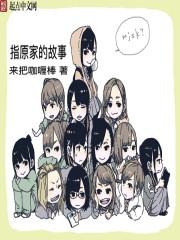凌乱的床铺示意昨晚的炮火之凶猛,艾玛静悄悄地抱着被子深陷睡眠,拓久则早已起来,穿好了衣物,拿起手机给斋藤长明发送了信息,让他在外面驾车等候。
一阵嘤咛,床抖动起来。
是艾玛醒来,翻了个身。
“要走了吗?”额前的刘海被她重新梳了回去,她光洁的额头很美,但是也有不足,如果不注意的话,被拍摄后会显大。
“是的,还有许多要处理的事情,你继续睡吧。”拓久安抚她一句,裤子上的皮带也被系好,准备到门口捡起昨晚进来时候扔在地上的西装。
整理完毕,拓久又穿回了昨天的衣着,精神昂扬。
“昨天我很舒服,甚至比以前更舒服。”艾玛突然赞扬起拓久,说完这话后,她又翻转过身子,趴在床上,健康苗条而又不失肉感的娇躯侧露在拓久眼前,无端地是诱惑至极。
若非确实有事,拓久可能会在这里再停留下来吧。
“你这么说我想我会感到很开心的。”拓久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艾玛的赞扬,这无非是对他能力的赞同。
先前也说过,美利坚是很开放的,所以即使艾玛今年才十八,就已经有过一个男朋友,自然也品尝过了禁果。而拓久也不是那种一定要没经历过才会上的人,即使在这之前和她有关系的人都是未尝过禁果的。
昨天只是情动片刻,两人都互相看得上眼,所以才会有疯狂的一夜,真的要说二人有什么关系?
其实也没有。
拓久只是艾玛普通的影迷,艾玛也不是喜欢拓久的青梅竹马。
真要说的话,就是所谓的炮(和谐)友。
他不会在意艾玛现在是否会和别的有关系,艾玛也不会关心他在霓虹是否有恋人。
这是双方的默契,不会在话语间提出来。
不过真要说有没有进一步的想法的话,那肯定是有的,艾玛的颜值各有说法,毕竟审美是主观的,至少就拓久本人而言,觉得艾玛很漂亮。
不需要太多的修饰词,只是漂亮两个字就足够了。
如果拓久是身在美利坚,在美利坚工作,与艾玛近距离接触的话,那么会有继续和艾玛产生联系的这个想法吧。
可惜他的大本营始终是在霓虹,美利坚对他来说也只是个过客罢了。
不切实际的想法还是丢掉好了。
异地恋什么的,无论是拓久或者艾玛,都是不会相信的。
“下一次来美利坚的话,也可以来找我。”艾玛这么说了一句,“明年如果考试合格的话,我应该会在布朗大学那里就读。”
“真是个才女啊,我这个世俗的商人到时候说不定就自愧不如了。”拓久还是没有马上离开,走回了床边,侧对着艾玛,手里抓住艾玛的小鼻子轻轻一捏。
“嘁,我也不一定能上布朗大学呢。”艾玛轻轻打掉拓久的手掌,两手抓着枕头,竖立着枕头,头靠在枕头上。
“也是,到时候的事情到时候再说吧。”拓久也不纠结于此,“什么时候你来霓虹的话我也可以好好招待你,带你体验一下霓虹的风景文化。”
“明年有机会的话,也不对,可能要10年吧,等新的电影上映之后,说不定就能借着这个机会去你那儿宣传,那个时候可不要装作不认识我哦。”艾玛悠悠说道。
“你别装不认识我才对吧?等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是个世界闻名的大明星了。”拓久失笑,不过还是应承了下来。
两人又在说了一会话,交换了各自的联系方式之后,拓久也就告别离去。
艾玛的住址外,斋藤长明早已在租来的跑车上等候。
上车之后,拓久又对了一下时间,因为多说了会话,比预计的晚了十分钟。
“久等了,我们走吧。”
斋藤长明轻点头,开到急速的跑车扬长而去。
剩下这几日,拓久就在做着善后的事宜。该做的他已经做完了,以及赚够了本钱了,更多的就不是他所能涉及的。那么呆在美利坚也没什么意思了,早日回霓虹也好。
善后的事情也很简单,就是在美利坚这边设立一个联系的平台,以便出了紧急状况能随时联系他。以及把原本作为保险抓来的,啊不,是骗来的女孩子还给了在上级部门上班的她的父亲。
虽然这个女孩子并不是很想回去,要不是强制地送回去,她可能还会在小屋子里待着不肯回家。
所以说玩游戏一定要适度,如果沉迷网瘾,不仅对自己不好,对家人也不好。
事毕。
到了回国的一天了。
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
指原的自立生活过得怎么样了?她和麻友还有柏木的关系又处理地如何?
有太多他不了解的事情,需要等他回国之后一个个去了解。还有伊达长宗和他打电话报告的,关于渡边宪和周防的燃系合作的事情,也要等他回国后去解决。
虽然不知道渡边宪是如何让燃系同意他的合作的,但是确实是有些棘手。
嗯,棘手。
他已有足够的资本了,渡边宪的那些手段在他眼里就如地下行走的蚂蚁,一脚就可以踩死,就是能不能踩到的问题罢了。
所以才说是棘手。
霓虹,我终于要回来了。
内心呼喊着,他的航班到了。
“有一句要问一下,斋藤,啊不,好歹共处了那么久了,我叫你长明不介意吧?”说完他也不理斋藤的反应,继续说道:“回霓虹后,你会继续当我的保镖吧?”
“只要老板你继续每月付足足够的费用,是可以继续延期的。”斋藤长明一如往常地冷漠,不过在话后面又补了一句。
“如果是老板你的话,或许可以给你打折便宜一些。”说到这斋藤长明嘴角突然上浮,又在以往的训练习惯之后隐去了自己的笑容。
“是吗?”拓久听完,“那么到时候就继续拜托你了。”
通道开启,拓久扬起步伐,缓缓走向了飞机之中。
他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走的时候也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