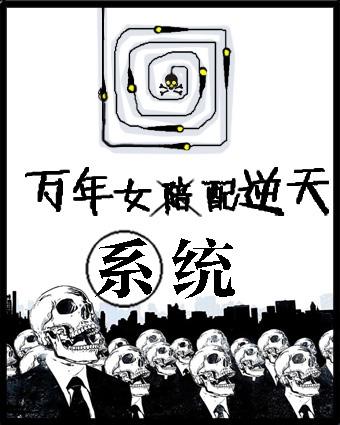.co 野旷天低,海动山遥,极目之处一片黑压压的人头马背,楚月璃摇了摇头,运一口纯阳真气先将小楼做下反八卦金刚结界,这个举动顿时令众人大惊失色。
姚初化毫不客气地伸出二指,怒道:“楚岛主!你这是何意!难不成你要庇泽这个恶贯满盈的妖怪吗!”
二师姐急了,大喊:“岛主!你忘了师父是怎么死的了吗!”
楚月璃就地打坐权当没听见。
八大宗师愤然退回本位将小楼围在当中,各方真气流汇并于中间形成天地定位、九宫对峙的元气场,其中一点空气凝重、八风阻滞,置于这一点上人如同在稠密的蜂浆中呼吸,这是专破反八卦金刚结界的金刚八卦阵,纯阳体质绝对不得活命,楚月璃正感吃力时,付雨裳与他背身打坐开始运纯阴真气,可是只运到一半便感到不济。
这时,含溪在结界外面喊:“相公!不要再和他们打了!快收手吧!”
楚月璃合目,道:“娘子,你到底是在帮哪一边?”
含溪哭着说:“我当然是帮你啊!我当然是为你好啊!”
楚月璃道:“为我好就不要再喊我相公。”
含溪顿时把话哽在喉中。
金刚至坚之物,金刚八卦术是至强之法,若是付雨裳没有受伤,两人一个纯阳一个纯阴置于八卦阵中间一点必能决胜八方,但眼下付雨裳只有五成纯阴真气,楚月璃的另五成纯阳真气势必会白白被八卦阵吞噬再分散到各位仙宗的体内助长八方,八方真气助长之后便会对中间一点产生更强冲击。在场的仙师都晓得楚月璃这是决意与付雨裳死在一处,但谁也不知道楚月璃还有一个自创的绝招“载术”,这便是当初他觉得自己能打赢付雨裳的筹码。
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而然、无状之状即是超脱阴阳笑傲八卦的载术。八卦尚有阴阳两极、载术却只有一个一,楚月璃称之为“载”,意思是一切的载体。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当下顿入不二法门,因此成就尽虚空遍法界的威力之鼎。借自然之力降服人道、地道、天道,区区几个肉身的仙师不过是人道中的一环,若是楚月璃当真运用了载术,必不会让八位宗师活到眼下光景。
付雨裳忽然发现楚月璃体内的真气浑然如一块儿玉璞、并不存在阴阳两极的往返运行,他仿佛正在翻来覆去地调转把玩一样东西,就像是一个新买回来的水杯到处找不到把手,付雨裳甚至猜不透他究竟在干什么。
不久,自信满满的八大宗师开始感觉到吃力,缘是结界中的元气场阳极与阴极互不通风,全被楚月璃阻断。姚初化年事最高最先支撑不住,一口淤血喷出来染红了银白胡子,接二连三地各位仙师统统顶不住了。
大师姐见状命令十二仙子打坐运真气给八大仙师,含溪不得不从,谁知此法乃是杯水车薪,十二仙子纷纷被中心一点浑然真气震裂五脏、口吐鲜血,多仗含溪并未用十分的诚意听从大师姐的话,受伤还算最轻的。见此败绩之景,朝廷兵马随后冲杀上去,人与马全被金刚罩碰得头破血流,方知结界并不是硬闯的。
桃花岛数千弟子背弃岛主投械而去,大师姐和二师姐抱在一起哭天抢地:“苍天啊——这是为什么!岛主究竟为何要加入魔道!师父啊,您的在天之灵是否看到了这一切!”
天空黑云遮日,地上狂风大作,朝廷的兵马将此地重重包围,刀枪鸣钺,马嘶喧天,眨眼间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御林军。
楚月璃收了真气,站在小楼屋顶上伤感地说:“此地不宜久留,雨裳,你可有藏身之处么?”
付雨裳道:“可叹天下之大藏身之处却无,但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好,我跟你去。”楚月璃刚要转身,听见下面有人在喊“相公——”。
楚月璃对付雨裳说:“等一下。”
付雨裳道:“那个地方她不能去。”
楚月璃点点头:“我知道。”
含溪哭着说:“相公,你忘了一样东西。”
楚月璃蘸蘸眼角,远远地望着她,竟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含溪,我……”
含溪从腰间抽出一把扇子,扇面又宽又大,是一把男人用的扇子。楚月璃霎时泪如雨下。含溪展开扇子,扇面上十个血字已凝成冷紫色。
此身今已定,相欺到死时。
这一刻含溪才发现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含义,是天意在作弄人,虽则含溪相信他当时只有一个意思。
含溪泣不成声地说:“小女子蒙楚王世子垂爱,此恩此情,无以为报,今日一别,山长水远,望世子多加珍重!”说罢,将扇子抛了过来。
可怜一代仙尊楚月璃在大风中并没有接住这把扇子,巴巴地看着它被狂风卷到了远方。
含溪的背影越来越小,再没有回头,少小夫妻怎堪相舍天涯独步,付雨裳抓了抓他的肩膀,楚月璃抛下一把眼泪,随付雨裳踉跄而去。
目睇烟霄阔,心惊岩壁高,但见脚下山色花野杂,湍急一条水带自古到今流不尽,崖壁清溪泻琲帘,谷中虎啸猿啼声不绝。千里一座孤坟立在悬崖顶上,坟头松云缭绕、鸟迹罕至。
楚月璃长跪于坟前,问道:“我爹是怎么死的?”
付雨裳道:“当时我与那八个人在定中斗法,千岁亲自挎剑守关,你师父莫万歆率领当时的颍王几千兵马与千岁的禁卫队厮杀了七天七夜,后来所有的禁卫都死了只剩千岁一人,千岁把我藏到王府南角的藏经楼中,而后拔剑自刎。”
楚月璃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师父为什么要那么做?”
付雨裳轻咳着道:“当年你师父被尊奉为‘囸极’,出仕朝廷后三年无功反而多过,舆论压力非常人所能忍,朝廷明着是为百姓除妖暗里却在争夺皇位,先帝驾崩传位于十岁的太子,亲王们都对皇位虎视眈眈,淮王在楚、颍王在汉、湘王在吴、洛王在许、浏王在陈……免不了一场手足相残。千岁封地在楚,府邸却一直没有搬出京师,用意甚为明显,且听说千岁主张道法治国无为而为,有志的仙师们纷纷来助他成事,我受紫微大国师之邀在京城协助降魔,幸遇千岁。而你师父在巨大的压力下终是投靠了颍王。后来我等助千岁取代太子自立为淮帝,一念仁慈留了你师父一命,然区区天牢如何关得住他的五行遁术,不久颍王借着‘妖在宫、清君侧’的名义造反,你师父便和八大宗师勾结起来助颍王叛乱。”
如今面对一抔黄土空谈过往曲直,谁肯来倾听,只有夙夜不断的崖顶风沙安抚故人惆怅的亡魂,楚月璃心如刀绞,至哀无声。
付雨裳走上前去用袖子拂去墓碑上的尘土:“什么妖,什么仙,雨裳已经不在乎那些‘名’了,千岁还在乎么?”石头墓碑默默无言。
付雨裳笑了笑,摸摸上面的“淮”字,道:“大直若屈,大辩若讷。千岁回答得真是聪明啊。”
楚月璃不由得泪湿衫袖。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谷深三千尺,空寂无人,回声悠远。一栋陈旧的宅院中没有明媚的色彩没有精巧的浮雕,一切都那么坚实质朴沉敛厚重、四处弥散着淡淡的古木沉香。一盏孤灯在矮几上绰绰摇晃,帘帏里铺着一床粗布棉被。
付雨裳替他把窗扇合严,道:“谷中终年寒冷,夜晚尤其凉,你没有蹬被子的习惯吧?”
楚月璃摇摇头:“没有。”
付雨裳笑道:“那就好。”
楚月璃见他已走到门口,又说:“谢谢你。”
付雨裳没有回头:“这里也不是长久栖身之所,我相信很快就会有人杀来的。”
楚月璃道:“对不起。”
“不过你随时可以将我交给朝廷把自己摘清,我为你死死得其所,只是一样,记得把我的骨灰与千岁合葬。”
楚月璃没说什么。付雨裳走了。
楚月璃打开窗户,此际,菊花谷底气温寒凉阴滞,方开四月之花,不禁令他想起了桃花岛,含溪应是随师姐们回去了吧,烛泪染萼,愁红满园,菊花谷相距桃花岛遥遥数千里,楚月璃如何睡得着,远处响起了依稀的古琴声,是付雨裳坐在崖顶墓志前迎风而弹,月中白鹇影过,旷古凄凉。
突然一阵骤咳代替了琴声,起初他心口上挨的那一掌并不要紧,只是随后他在大雨里淋了一夜,染上风寒加重了伤势,小南国又替血凤接了一掌真气,这就十分不妙了,及至后来在屋顶上与八宗斗法,动本伤元、难以回天。
楚月璃将一条雀翎披风披在他肩上,双眼湿润:“雨裳,我不要你死,你活下去好不好?”
付雨裳笑着点点头,继续弹琴,直至一曲终了都没有再咳,最后却吐了一口血。二月榆落,八月麦生,星辰欲变,人将奈何?轰轰烈烈的人物未必死得惊天动地。不过,能够在最后的日子里和这个人在月下对坐而望,好似回到从前那般相恋相守的光景,已令付雨裳感到三生有幸、百世无憾。